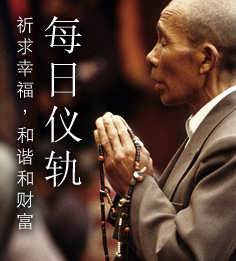金刚体虚空当中的降世明王三密,
如同日月闪耀,我的护法,那位仁慈之主,
天赋一双、20种功德,
愿您脚下的尘土触摸我的头顶,直至我获得正觉!
无尽的轮回,由无数恶业和痴妄结成的亿万绳索,
千变万化的图像,披着各种各样、就是没有幸福的外衣,
让人心惊胆战!
然而,就像黑夜划过一道闪电,无暇的法道稍纵即逝,
却能投向圣者的仁慈之心,赋予轮回再生以深意!
然而,内心对恒常和真有的魔念,死抱不放,让心灵不断流浪。
因为此生的各种顾念而心不在焉,恍如观看猴戏,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最高目标随风而去!
我是一位常人,名叫罗桑耶喜丹增嘉措,人们认为我是第69任甘丹赤巴赤钦蒋秋丘帕转世,以及第85任甘丹赤巴赤钦罗桑帕丹(Päldän)转世。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心灵我是很清楚的,我知道我远未达到那样的证果,不配做这两位圣者的转世!但是,由于前世的巨大业报,我命中注定要取得他们转世的称号。就像Je 贡塘pa所说的那样:
如果杜固为了众生和佛法而出世,
他们的教诫和修行应当留下痕迹!
你看到前世圣者的行迹,你会受到震撼!如果你听到他们的事迹,你的信念更加坚定。这样,就有了强大力量,它在受训者的心中打下解脱的印记。可像我这样的人,心中充满困惑,受到三毒的侵害,只知道三时,这无益处可言,就好比乌龟身上找不到毛发!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功德,但由于我要背负喇嘛之名,通过学习、观想和修行,以免虚度生命,可以自称在维护和弘扬佛法方面,也留下了一些产生影响的印迹。此话如果不加详查,仿佛还能说得过去,但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我所产生的影响经不起挑战。我的本性就像彩虹的诸般色彩,没有哪一样色彩能够挑出来!因此,让我来写自己历经坎坷的一生,就仿佛东施效颦一般模仿前世的高僧大德,就像一只蝙蝠,假装自己是雄鹰!会贻笑大方!
虽然如此,1964年(藏历木龙年)在西藏天人共同的主牧、降三世明王、皈依主护法嘉杰帕绷喀德钦宁波(帕绷喀金刚持德钦宁波) 尊者对我说,我必须书写自己的生平传记。我顶礼膜拜,恭敬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后来,一些虔诚的弟子如Je Trehor Geshe Tamdrin Rabtän等也强烈要求我写出来。 Kazur Kungo Neshar Thubtän Tharpa 还向我进献了佛像和哈达敦促我书写。Dragyab Hotogtu 仁波切 还从不远的Jarmän地区写来了一封信,强烈要求我动笔书写。另外,长期住在我附近的邻居帕丹(Päldän)还详细完整地记录了我的情况,自始至终都是如此,而且是通过他亲眼看到的事件,另外加了他所听到的别人的评述。我仿佛没完没了地用他所做的记录印证有关事件。
Kyishöd和Tagtse从前的一名贵族、Zhabdrung Dorje Namgyäl、众位大臣、Kalön Gazhiwa Doring Tänzin Päljor、Kalön Dokar Zhabdrung Tsering Wangyäl,还有其他一些官员和重要人物都曾写过自己的传记,因此,据我估计,不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加以记述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
由于愚昧无知加上遭逢的黑白业力,苦乐相续,四季相伴,而且虽然我的一生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浪费了美好人生的自由与良机。我从仿佛菩萨再世的灵魂导师那里,受获了广大深奥的佛经与密续教诲,而且没有把那些教诲们当成过眼烟云,而是不断修习,将其融入自己的灵魂; 但没有哪一点佛法我能够充满信心地说自己已经完全领悟。正如无上降世明王、第7世嘉瓦仁波切Kelzang Gyatso所言:
据说,没有达到佛法与心灵合二为一,证得功德,
却假装帮助别人、给他们指点解脱之道,
只让自己和别人筋疲力尽,
也是让自己遭受奴役的不二法门!
因此,仿佛一台录音机,仿佛鹦鹉学舌地念着《嘛呢经》(MANI mantras),我记述的经历对众生毫无益处。简言之,就像西藏的上师Mipham Geleg所说,
尽管我们觉得自己心中有一片祥和宁静的森林,
如果我们道德历练不纯,靠一根弯曲的拐杖走路,
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那么,就让我吞下如此不仁之举的恶果吧!
我不会用世间八法污染这个故事,也不会假装某些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或者假装自己做过什么未作之事,以延续福业、非福业和杂业(mixed karma)的轮回,从而达到自得其乐和蒙蔽他人的目的。相反,我要用通俗的散文,直截了当地讲述我未受佛法时身无一物、空着双手到处游荡的经历。
我出生的地方,西藏,受到手持莲花的上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教化。我出生在西藏三大地区之一、名叫卫藏的中央佛土四个地区之一的贡塘吉雪(Kyishö Tsäl)。 那里出生过一位名叫众生护法Shang Yudragpa 的喇嘛,他在当地修建的梵苑成为巨大的修学中心。文殊护法宗喀巴建立许多格鲁派佛学院之前,Shang Yudragpa所建的修学中心是西藏中部六大佛教社群之一。它称为贡塘Tsäl,熟语”Sang De Gung Sum, Ga Kyor Zul Sum”当中提到过它。
Tsälpa法座持有人的权威曾盛极一时,当时Tsäl包括中央地区和两所称为”客山(branch monastery)”的佛学院。贡塘的Tsäl 有三所佛学院,分别是 Chötri、Zimkang Shar和Chökor Ling佛学院。因此,从宗教和政治的角度而言贡塘佛寺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Tsälpa Tripön的权威却下降了。第60个甲子轮回的火兔年即西历1507年,贡塘发生了火灾。那次大火烧毁了一些非常神圣和具有标志性的物品、整座中心庙宇、大佛像、Zhang仁波切像、”Tashi O Bar”的灵骨、四臂大黑天的佛像等等。由于只剩下规模比较小的Chötri和ZimkangShar学院,该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重要性大为降低。5世嘉瓦仁波切在位期间,Zurchen Chöying Rangdröl乃法座持有人。
后来,第50任甘丹赤巴、青海出家人Gedün Püntsog给宗喀巴大师舍利塔镀金时,拉藏王(King Lhazang)赐予他管理贡塘寺及其诸佛像、两所佛学分院、供物以及全部土地、房舍、人众和财产的权力。为此人称他为”崔钦贡塘帕(Trichen Gutangpa)”。他的历次转世如伽梵Tänpay Drönmay 仍被人们称为贡塘仓,他的名字也如雷贯耳。然而,崔钦贡塘帕的一些转世主要住在安多Tashikyil拉章的时候,由于距离遥远,他无法管理贡塘寺,于是政府将其收回。
后来,在7世嘉瓦仁波切Kelsang Gyatso年轻的时候,贡塘帕的转世是嘉瓦仁波切的叔叔 Ngagrampa Samten Gyatso,同时担任嘉瓦仁波切慈爱的仆从和阅读老师。
他后来又转世为博学的蒙古达尔汗寺住持、”沙皇(Tsa)”后代Gelong Kelsang,他受到无上尊崇,国王竟把贡塘寺及其圣物永世赐给了他。
毋庸置疑,Tsering Döndrup是7世嘉瓦仁波切叔叔家族的人,而且是贡塘拉章的成员。这个拉章的成员都学识渊博,精于数学,他们与人进行的俗事交往也很诚信可靠。Tsäl贡塘寺地方的人都十分尊崇Tsering Döndrup。他们尊他为智者,向他寻求解决疑难问题的答案。
Tsering Döndrup生了5个儿子 ,其中包括 Serje Prati Kamlung Tritrurl,还让两个女儿生到 Lanpa家。孩子们的母亲去世后,他又与一名女仆生了一个儿子,人们认出这个孩子是Ganden Pukang Kyenrab杜固。前面提到的5个儿子当中最小的到了大约20岁的时候,与来自贡塘”Nang Gong” 家族的Tsering Drölma, 即我的母亲结了婚。可他的这位儿子后来在去拉萨的路上、在过Kyichu河的时候淹死了。
Tsering Döndrup不忍抛弃自己的儿媳,便娶了她。这桩婚姻给他们带来了3个孩子,包括我妹妹Jampäl Chötso,还有据说Lelung杜固的转世是我的弟弟。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大的。
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 Tsering Döndrup 59岁,我母亲Tsering Drölma 27岁。由于先前累积的善业,我出生在1901年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太阳从东方破晓时我正好脱离母体。
贡塘拉章管理着贡塘庙和两所佛法学院,因此我出生的时候有许多要人在侧,当中必须有一位剃度的官员作为政府的代表。为此,事先举行了一场宴会,出席者有前任政府财务主管、Jampa Tängyä。后来,我记得还有一位十分有名的联络官名叫Kändrung Gungtangpa Tenzin Wangpo。
我有一个姐姐名叫 Kelsang Drölma,她嫁给了Ger Kemepa 的儿子,名叫Rinchen Wangyäl。告诉那位地方政府代表之后,他说Keme和贡塘拉章的福祉应当合而为一,并给它取名叫 Kegung。由于我的两个政府联络官(一名居士、一名僧人)要回到拉萨履职,到我3、4岁的时候,有人在拉萨堪察了一块土地给我建了一所新房子,后来名叫 Kunzang Tse。
大约在我3岁的时候 Kändrung Tenzin Wangpo 和我父母才接受了管理之职,贡塘庙的上中下层进行了大面积的翻新。同时也对嘉瓦仁波切所住的的顶层卧室和外院以及其他建筑进行了修茸。
这期间名叫Tzamling Chegu Wangdü的Sakya Puntsog Podrang受邀来到贡塘庙主持长生灌顶与净障。他把几粒长生丸放在一只银匙里。举行净障仪式时,在大锅里点上火,人们把大锅来来回回地抬。然后,他把一只陶像放在我头上,从长生瓶里洒水浇那只陶像,以此来给我沐浴。一位年长的Sakya女士把我放在她膝盖上,对我露出讨好的表情。这些事情我依然记得。
我37岁的时候朝拜了藏(Tsang)区。此前,他们已经在Sakya Puntsog Podrang的一个圣所内室,展示了那位做了长生剃度的高僧的遗骨。在给他火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迹:脊柱化成一朵莲花,直径有手掌大小。
我的前世 Lozang Tsultrim Päldän 于1839年出生在 Tölung Ragkor 的 Wöntön Kyergangpa 家族。1896年是火猴年,他升上金法座,成为甘丹赤巴;铁鼠年(1900年)他任甘丹赤巴期间,第13世嘉瓦仁波切到了Chökor Gyäl,大家决定让他沿着上方的路去甘丹寺。根据惯例,这位 甘丹赤巴先行动身去拉萨,以护送嘉瓦仁波切上路。 还是根据惯例,他带了一小队随从和一只黄伞。这位甘丹赤巴快要到达甘丹寺的时候,来到贡塘拉章的柳树林,说要在那里休息一会。由于现场有一小队随从,有人问他随从们回到村子附近他们自己的住处是否合适。他回答说:”在这儿呆一小会儿有什么不好?” 并把动身的时间推迟了一会。他还说:“我去甘丹和回来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个熟人,这里就是途中歇息的好地方,不是吗?”
后来,在甘丹寺举行完仪式、并且去了Chökor Gyäl后,这位甘丹赤巴生病了。他每天绕行甘丹林的道路,同时随身带了一个小法座、金酒配备、水供等等。1901年,他接受邀请的时候,沿着那条线路走来,并在法座室里坐在法座上,身边跟着几个近侍。Lozang Tsultrim Päldän当着侍从们的面与自己的 Changtzö Ngarampa Gyütö Lozang Tendar 交谈。他讲了很多,比如“这个人(Ngarampa)会来找我”。后来,他把目光转向西方天空,大笑着说:“哈哈,甘丹,甘丹”。突然,他当场过世了。
当时,桑林寺的格西Nyitso Trinle 负起责任,把圣体送到大喇嘛的居室,以进行最后的明光禅修。把圣体尊崇一周之后,在甘丹Gogri山后进行了火化。 风和烟雾把火葬室屋顶的天福伞 [mentse (peak benefit)] 吹跑了,它飘到高空。最后,伞和烟都向西方飘去,飘得又高又远。
一周后,火葬室的门打开时,圣体的心脏、舌头和双眼都完好如初。乡城人把这些圣物拿到当地的寺庙里是为了在一座正在建的塔里加以供奉,但却与汉人发生了争斗。一开始,乡城人给那些圣物进行了沐浴。可后来他们却发现饮用浴汤和祭祀那些圣物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由于需要使用圣物对抗汉人的刀枪,所以就用浴汤浸泡食物等。后来,我的Changtzö Ngarampa还批评那些乡城人,说他们是“吃掉我喇嘛心的人”!
后来,Changtzö Ngarampa尊者和他的助手Chizur Legshä Gyatso来到已逝大喇嘛的圣物前,举行了“供奉云”仪式以悼念他的离去。负责寻找其转世的Tugen Kangshe要求撰写祷文以呼唤这位伟大的皈依豪尊赶快回来。于是,Changtzö Ngarampa便立即坐到Yabshi Lang(这位已故喇嘛出生的房子)跟前进行撰写。
接着,就在我刚要出生的时候,生长在贡塘拉章Trokang柳树丛中的一棵梨树竟然在冬天开花。上面结了30颗梨,就像古代收获庄稼不用耕种一样。我出世后,从开始走路之前,就对觉尊的塑像、画像、话语和意念十分崇敬。我对供奉器物如金刚杵、铃、鼓和铙钹等很喜欢,并且喜欢僧人的用品。我想要加入僧人们的众会行列,并且喜欢模仿他们诵经。
由于这种行为显示了来自先前诸世的一些良好印迹,经常来贡塘拉章做法事的甘丹 Lhopa Geshe 尊者说:”贡塘 拉章 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男孩,你们在寻找杜固的时候应当把他也算上”,还说应当对他进行认真考察。
Ngarampa 和名叫 Sadül Gedün Dragpa 的乡城格西第一次到贡塘考察那个孩子时,我的保姆正巧站在门外,我则骑在她脖子上。我们走近他们时我大声喊道:”Gedün Dragpa!”
Changtzö Ngarampa问贡塘拉章的那一带有没有一个叫 Gedün Dragpa 的。我的保姆回答:”没有,一个也没有!”
听了这话他们感到非常惊异,而且,等他们进屋后我爬上 Gedün Dragpa 的膝盖,伸出双脚命令:”洗!”
前世生病的时候,Gedün Dragpa 就是那个用萝卜汁给他洗脚的人。这让他回想起前世在世时的情景,于是他一面眼中流着泪一边洗我的双脚,还用舌头舔!我知道今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但是,除了这些祥兆以外,我对自己前世的情况已经完全忘了。
拉章放养牲口的人叫 Tashi Döndrup,Lhau 和 Päldän的父母(他们是那位喇嘛前世最贴身的两个高级近侍)听说 Tsäl 贡塘 有一位杜固时,正在去往拉萨的路上。由于他们对主人的前世极度信仰并且十分热爱,于是便过来仔细对我进行观察,并且对他们自己做了介绍。我在贡塘拉章有一间小卧室,墙上有很多面镜子,于是我向他们跑过去,给了牧羊人一枚银币。牧羊人觉得自己不该拿那枚银币,于是要还给我,这时我父亲说:“这是孩子给你的,所以你能拿着”。我记得他当时说了这话。
关于第13世甘丹赤巴尊者的灵童,第一次得到卦辞是这样说的:”到水虎年(1902年)2月,看看拉萨南部法派便可。”当时我母亲刚好去了拉萨去做礼拜和绕佛之类的修习,我舅舅 Aku Trinle 则正在管理拉萨南部法派的一所房子,于是借了一间给她住。Yongzin Phurchog Jampa 仁波切 占的一卦表明,灵童就在离甘丹寺不远的地方。Gadong 护法的神谕神谕的第一个嘱累是:”在寺庙东边附近找一个铁牛年(1901年)出生、他母亲名字最后一个字是 Drölma 的男孩”。
林金刚持仁波切上次示现占的卦说:“在身、语、意、功德和事业五个化身当中,心的化身在离拉萨南面一个不远的地方”。他又占了一卦,这时示现了可能是灵童的小孩名单,结果是:”认定铁牛年出生于贡塘 Tsering Drölma 家的男孩便是殊胜者”。
Gadong神谕的第二个嘱累是:”可以认定铁牛年 Tsering Drölma 家出生的男孩是灵童”。 有人请涅仲神谕给出带名单的悬记,结果与前面说的名单一样:Tsering Drölma 铁牛年生的男孩。
Changtzö Ngarampa 和其他几个人对我进行初步认定考察的时候,拿出一尊佛像给我看,那是前世甘丹赤巴一直保留的遗物,另外还有念珠、钵,还有另外一套同样大小的物件。我第一把拿起来的是佛像,我拿对了。他们认为这表明我同意做佛法教义传承人,是吉祥之兆。我还拿起钵,也拿对了。到了挑念珠的时候,我先是拿起一串假的,然后又放下,拿起真的。另外一串念珠是它的主人没有送人而是留在身边的,所以他们坚信我就是那个灵童。
同时,乡城的上厢房里住着 Chagong Beda Troti 一家,他们也有一个显示出灵迹的男孩,于是希望认定他们的儿子为那位伟大法座的灵童。还有,在 Tsäl 贡塘 地区,散布着这样的传言:Changtzö Tzongzur Legshä Gyatso 的儿子将被认定为杜固。 后来乡城寺院向拉萨的 Changtzö Ngarampa Dampa 和 Tzongzur Legshä Gyatso 送信,内容是“喇嘛的转世就在乡城,因此你们在贡塘没有权利,不得认定贡塘的小乞丐”。可赤江拉章 答复说:“是我们照管乡城寺院、土地和财产,你们两个不得接管!”。
在和甘丹寺和色拉寺, 乡城的代表们也持不同观点。有些人则漠不关心,说最好准确无误地认定转世的灵童而不论他来自哪个地区。但是,多数人认为应当认定他是乡城的孩子。
由于当时莫衷一是,大法会期间,甘丹萨济寺扎仓的住持、喇嘛官、Dokang 康村和桑林寺的代表在拉萨的拉章开了一次会。会一连开了好几天。 最后,政府敕令到达——根据嘱累和占卦结果还有上师及本尊的意图,确定认定的人是我。我的房间里保存着早先和后来发自乡城、写了我地址的信、从乡城发出的那些信的草稿、西藏中部的上师和本尊发出的正式嘱累和占卜的卜辞、为了找到确定的杜固而做的众多法会记录,还有前任法座逝世以及我认定过程和入寺之前所受照顾的情况记录。后来,这些材料都转移到Chuzang的闭关处。
由于拉萨所作的决定,有关方面受命认定我为杜固并继承前世高僧的法座。乡城除了几人始终不服外,大多数人都认定我是灵童。
尽管听到有人提出抗议,但1905年晚些时候,汉人将军Drao Erpung (又叫 Drao Tarin)的庞大军队还是袭击了许多该地区的寺庙如 Litang 和 Ba Chöde。特别是乡城寺,经过长时间的攻打,最后于1906年失守。许多僧人与居士被杀害。这一地区得以逃生的僧俗逃到森林里,藏身在那里并继续反击汉人。直到1918年接近年末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陆续聚集在已经沦为废墟的中央会堂。
同时,由于该地区长达13年都战乱频仍,其他派别的谎称也自动长期偃旗息鼓了。因此,到1918年我接受格西拉让巴 的称号时,该地大多数民众都信仰我。然而,后来,到1928年,我28岁时,Beda地区的一个派别重拾旧的谎称。我想详细讲述这一情况,但仅说这一句就够了:即使 Vishnu 亲自示现千臂,也不能改变这种极业!
1904年我4岁,离开出生地,被带到拉萨的赤江拉章。那天,一大群剃度和在家的官员事先已经聚集在Kyichu河的岸边。按照传统,甘丹赤巴在大法会结束时进行了灌顶加持。他们正要返回时,我们一班人与他们相遇。这事发生得很偶然,没有进过事先计划,而是水到渠成,仿佛他们是来护卫甘丹赤巴的,人们于是开始谈论那个迹象十分吉祥。
我们走近拉章的时候,看见一个姑娘背上驮着一包麦子。由于一大帮骑马的人向她走近,她分了神,于是手里拽的带子从她手中滑落,麦子撒到地上。滑出的麦子完全挡住了拉章的入口。于是所有护送我的人都觉得这是个祥瑞之兆,便抓起麦子抛向空中,仿佛拉章向佛法与众生之主进行初供。
我们到达我的僧房时,有一大群人排着队,于是举行了开门就位仪式。为了吉祥的缘由,我的法座被摆成坐南朝北的方向,以便前来欢迎的甘丹寺喇嘛官员们能够坐北朝南。有个名叫Togpa Kädrup的人与甘丹萨济寺的会众意见不一致。他与一个名叫Kamtrug的乡城保镖结成联盟,Kamtrug放弃了对前任 甘丹赤巴许诺的三昧耶戒。我看着 Togpa Kädrup的脸,用手指指着他,其实已经碰到他的脸颊了,表明他应当对自己感到羞耻。现场的人十分震惊,说他的脸变了色,露出惭愧的神情。
几天以后,Ngaram Dampa, Tzongzur Legsha 和其他人都来迎接我首次到达Chuzang闭关处。我眼前的景象看上去仿佛是一顶金色花环,只见许多修行很高的比丘身着黄色百衲披身和九衣(namjar),头戴班智帽前来问候和护卫我,当中有那位白发的年长喇嘛名叫Dromtö格西仁波切,他曾向嘉杰帕绷喀金刚持授受佛法。面对满座的僧人,我的法座背西朝东。我后面的一个法座上摆放着茶水和米饭。僧众们举行了吉祥仪式以祝我长寿,包括祝福加持、礼拜和供奉。供物当中有16尊阿罗汉的器物,其中有一条带猫鼬图案的织锦,非常好看。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把它握在手里好一会、然后交给别人的情景。
10天后,Changtzö Ngaram Dampa 伽梵说如果我在西藏传播佛法会是一件祥瑞之事。他一边说那就像以前的译师在纸叶上写经文,一边给了我一块特制的小黑板。上面是他用藏文楷体写的藏文字母表的30个字母。他在最下面还写了一些文字,其中包括如下内容:
Mi yi mig gi ri yi trin di rig
人的双眼认识这座云山
Tsun chung chung chung bum chung bum chung kur
那位小僧人背着几十万只小瓶
Bande re re se dre re re kyer
每位僧人背着一蒲式尔的东西。
他凭借那个助记工具,还有那30个字母作书写经卷的范板,开始叫我认字。我当天就学会了识别所有的字母,这让 Dampa很开心。后来他骄傲地告诉别人我一天就学会了所有的字母。
接着他继续教我依照《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Eight Thousand Verse Prajnaparamita Sutra)和《Son Kadampa Scripture》进行书写。他还长时间地通过让我修习阅读一部手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认字。那是Panchen Chögyän的一名声闻弟子写的,里面有多得数不清的缩略语。由于他仁慈地让我经过如此艰苦的修习,我每天都很轻松地读诵整部经卷而无论经卷的语言是多么优雅或复杂。
我呆在Chuzang闭关处时刚说了一句:”Tzong Kusho来了!”Changtzö Tzongzur Legshä Gyatso就到了,他从拉萨来,来之前没有通知。又有一天上午我说:”Lhundrub死了!”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曾经出家、名叫 Lhundrub、在 Mäldro Jara Do 看管土地的人死了。Ngaram Dampa 特别感到惊讶,还对此事作了记录。有人认为我本来应当在孩提时代就说出这些话的,但由于从我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预言,因此这情形仿佛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猪头竟然能说出预言。我连晚上排泄的粪便出自什么食物都猜不出来,怎么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 Tsering Dondrup 从江孜寺Chöje Kyenrab Yöntän Gyatso Pälzangpo那里受获具足新戒后便退位了。他的戒名(号)是 Kyenrab Chöpel。他供养我母亲Tsering Drölma 和我的两个弟弟和妹妹——妹妹 Jampäl Tsötso 还有最小的弟弟,给他们留下生活费和一片靠近我叔叔 Chotri Gelong Gyatso 住所、名叫贡塘 Chokor Ling 的耕地。
我6岁的时候,Tanling Demo仁波切来到 Dechang Loka-la 在 Chuzang闭关处的住处。有一天我们邀请他来我的僧寮。Demo和我初次见面的那一刻,就像同桌的同学那样,我们不知何故,竟双双泪流满面。我们的执事 Changtzö Ngarampa和Tänling Dechang Lokä 都觉得Tängyäling拉章和我们的拉章之间从前任甘丹赤巴赤钦蒋秋丘帕的时候起就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然而我的前任却曾经批评那些推举前任Demo仁波切 为西藏国王的人,结果,那些人遭到监禁并且死在那里。很可能出于对我们前世的这一痛苦情形的回忆才使得我们哭泣,但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些。
凭借前世集聚的功德和祈祷产生的威力,就像一块巨大的金石滚到我门口一样,1905年,无上尊妙和显著的帕绷喀金刚持来到Chuzang闭关处。他住在我们佛法庭院的起居室达7年之久,直到1912年末。当时他29岁,刚从上密院请假回来。在他有着Sölpön-la称号的哥哥之后侍奉他的只有另外两个随从。年长的名叫Changtzö Ngawang Gyatso,Shöl 的 Tashi 家出的侍从名叫 Lozang。有时候色拉寺的烹饪大师Gyälrong Geshe Tsangyang会过来做菜。他会呆上一两天并派出厨师。Gungtrul 仁波切 Kyenrab Päldän Tänpay Nyima、Pänpo Gangkya 仁波切、一个来自康区、名叫Minyag Rikü 仁波切的喇嘛,还有 Chuzang的喇嘛们如Dromtö 仁波切等,时不时会聚在一起交流佛法。他们有时候也会给色拉寺等寺庙的20到30名僧人传法。同时金刚持常常闭关并在闭关结束时举行法会。这位珍妙的上师亲自撰写炉边教文,安排供物,搅动并制作4种水供(stirred and made the four water offerings)等等。我当时很年轻,除了观察外,也会争着帮那位 Sölpön摆上和撤回供品。
当时那位珍妙的上师除了大量的经卷外身无长物,而他看上去也与普通僧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上午,我在学完了经卷之后直到中午都是放学时间,于是我便在院子里玩耍。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来到Kyabchog金刚持面前,带着孩子特有的意识,没有对他表示尊敬与崇敬。我在他面前跳贡塘灯舞、供花舞,有时还会在他膝盖上打个盹。他特别善于绘画,指导我在纸上画各种图形。他还叫人给我做了个和他同样的法座,让我在吃饭的时候坐。尽管我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但仁波切喇嘛的心性非常平和,从来没有丝毫的不快,而是愉快而且慈爱地照顾我。如今,当我回想起来才发现,这位无与伦比的慈父上师当时给予我的是博大精深的教诫。
尽管我修习时不能达到上师的理解水平,但却像萤火虫模仿太阳那样仿效大德。就像”用父亲的话”这个比喻那样,我做了大量的念诵,复述这位上师的语言,就像他那样寻思教授和传播佛经和密续。内容主要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我想到自己面临的机遇——从第一次认定我为灵童直到我获得格西学位(除了他无上珍妙的法身过世——那仿佛佛法的宏旨精义受到了堵碍)都一直与金刚持在一起并竭尽全力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侍奉他,我孩提时代单纯愚昧的行为没有错失方向,而是转向德行,这在我看来说明了此生和未来诸世所有功德的福根都是源于与这位上师的佛缘。
Ngaram Dampa 让我背诵的第一篇经文是《Expression of the Names of Manjusri》。每天早上他都会让我不停地背诵,直到我记住为止,风雨无阻。他让我背诵的另一篇经文是一篇黄色较短的《文殊菩萨仪轨》并背诵智慧心咒与明咒以增长智慧。为了增长智慧,我每天早上会在无人督促时主动坚持念诵那些经咒并计数直到最终慢慢达到10万次。
有一次我的哥哥 Trati Kamlung仁波切从色拉寺来到Chuzang向我介绍了他自己。他有一页很长的纸张,上面还有字母表,让我学习阅读。他还以为我在打基础呢。可发现我已经在背诵《入菩薩行论》和《现观庄严论》中的许多经文时,既觉得尴尬,又感到高兴。
在我当时那个年纪即使念诵经文都是极其困难的,但Ngaram Dampa 宽严并济的教学方法非常好。另外,对我来说,当记忆经文时,即使不知道自己记忆的词句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是用自己杜撰的意思去理解,那些词句也会立刻在我脑海里打下印记。当我请Ngaram Dampa教我那些词句的意思时,他会说记忆等修习方式能聚集所有理解经句所必需的祥瑞细节。
我7岁的时候,与 Ngaram Lozang Tändar尊者、Tzöpa Chizur Legshä Gyatso、甘丹萨济寺Dokang康村乡城Nyitso Trinlä Tänzin、Nänang Dräshing Geshe、Sölpön Püntsog 等人离开Chuzang闭关处,经过Pänpo Go关口,去Langtang寺住一段时间。
后来,我们穿过Chagla关口,经由Phödo到达 Ratreng Gepel Ling。我是在那儿领受Jetsün Ngawang Yeshe Tänpay Gyältsän Pälzangpo授戒的。他给我取了 Lozang Yeshe Tänzin Gyatso 这个法名,撰写了一篇优美的长祈祷文送给我,还把《现观庄严论》和《中观》(Madyamika)的读传送给我;我就是这样领受他的恩慈的。
当月 Ratreng 地区有一场法会,我们观看了刺绣唐卡的展示、戏剧表演等等。这次法会期间,我们朝拜了 Ratreng 地区的大小寺庙,以瞻仰最为尊崇的神器,如觉沃密集文殊金刚(Manjusri-vajra)塑像等并奉上千倍供品。我们还瞻仰了 Ratreng附近的 Tsenya闭关处、Yangön闭关处、Tsüngön Samtän Ling和其他地方以示恭敬并供奉。我在学识字的时候已经读了两遍《Kadam Buchö Son Scripture》,因此知道 Prince Könchog Bang的生平事迹。Ratreng各地的看管人一讲出各地的历史,我的脑海中便立刻辨别出那些地方。我练习阅读《Buchö scripture》的时候,Ngaram Dampa 还给我初步介绍了那些传记当中的一些故事。此后,我阅读传记的其余部分时,就能自动从那些简单易懂的诗句和大多数事迹当中大致理解其道。同样,我在背诵《入菩萨行论》时,能够从自己所记忆的《入菩萨行论》词句的大致意思当中,理解大道的主要内容,所以我在那个年纪已经对于尊者们的智慧有所领悟。
我们在Ratreng的时候,拉章负责人将带窗户的拉章住所上层让给我住,并且热情周到地接待我和我的侍从们。我们在返程途中在Taglung寺呆了一天,仔仔细细地考察了上庙和下庙以及圣物。我们还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一尊Dromtonpa 的雕像头上竟然长出头发!
然后我们顺着 Panpo 的大路往前走,沿途经过Thangsa、甘丹寺、Chokor 等地,最后到达Dromtö。我沿途吃的是他们在Ratreng给我们灌在皮囊里的酸奶,一直撑到 Dromtö。接着我们又返回到了Chuzang闭关处。
由于Kändrung Tänzin Wangpo 和我们一派的其他僧人和居士都在拉萨的更松次(Künzang Tse)定居,我动身去 Ratreng 之前,他们就留下了代表们住在贡塘。这些新住户当中有一个人是我父亲的兄弟、名叫 Ane Yangtzom-lag 和他妻子、康巴人 Bapa Apho-lag。他们在年长的Kün Tse官僚、Kemä 的儿子面前污蔑我母亲,要把她赶走,说她偷了东西。我姐姐也助纣为虐,终于有一天 Apho-lag 突然来到我母亲在贡塘Chökor Ling的住所,封了门,把我母亲和她两个孩子赶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好呆在 Zhangpo 叔叔Gyatso-lag 家,Gyatso-lag 叔叔给他们饭吃。这情形就像Jetsun Milarepa 的母亲Nyangtsa Kargyän 和她姐姐Preta Gönkyi,她们也经历了巨大的苦难。我们得到这个消息,Changtzö Chizur Legshä Gyatso就立刻赶到Kün Tse官僚的家里,一步步地解决了那一危难的情形。终于,门上的锁打开了,在彻底清查了财产之后,发现没有财物丢失。
我们听说了我母亲经历的苦难之后感到十分难过和担心。那年夏季闭关期间为一年的佛事做准备,由于Ngaram Dampa 懂得天文学和相关的经文,他便推算必须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来消除新月之夜的黑暗以及不详契机造成的负面影响。7月3日,Ngaram Dampa、 Changtzö Chizur、Tänling Dechang Lokä、 摄政Tsedrön Jangchub Norzang和一帮衣着亮丽的人骑马离开拉萨的拉章。虽然我们为留下管理贡塘的拉章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于Ane Yangtzom 和他带领的工人疏于管理,我们在贡塘Chötri扎仓的上室呆了一天。 那天,因为我的马挂着金色鞍辔,我身穿”鸦眼”锦缎法袍、头戴宽边唐闸(tangzha)帽,等等,在我一个小孩子看来,那仿佛是非常开心的时刻。第二天我们离开了贡塘,在Dechen Sang Ngag Kar的下密院住了一天。Sang Ngag Kar扎仓的人热烈而程序复杂地迎接了我们,一些住在附近的人前来祝福并进献了哈达。
第二天,甘丹寺Dokang Samling的几个人在anden Zhölsong修处的树林里搭起几座帐篷,建了一座营地,还带去了吃喝等用品,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天。次日凌晨我们起身,Dokang康村 已经用Serkang田野中的许多打谷房搭起大面积的宿营厨房。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聚集了许多康村的僧人和上师,他们带来了茶和米饭,觉悟身语意像,哈达等等。
头一天有人给我讲了许多可怕的故事,讲的是Dokang康村 有一位上师他动不动就发怒和打小孩。那天我看见那位上师本人,只见他嘴唇上一付大胡子,面色黝黑,挺着一个大肚子。可当我遇到他的时候,心里却在想:”这个不会是他们昨天说的那个!”于是我一点不感到害怕。
我们到达Tsang的时候,甘丹萨济寺已经在Shönbag的套房里用许多帐篷等东西搭起了很大的欢迎地。甘丹萨济寺和 甘丹江孜寺的住持和前任住持站在前列,领诵者和其他官员、两个扎仓和他们的全体转世喇嘛都列队在我的居室门前进献哈达。我刚看见甘丹江孜寺的Tridag 仁波切,还没有人引荐,于是就想:”这位是Tridag仁波切!”仿佛我们已经见过似的。
甘丹萨济寺扎仓向所有列队的人进献了茶和米饭,觉悟身语意像,哈达等等。那些僧官和扎仓的僧侣也进献了茶和米饭、觉悟身语意像。
接着,我们与那些迎接我的转世喇嘛一道继续赶路,他们骑着马,穿的僧袍设计非常繁复。到达Drogri山以后,喇嘛们和甘丹的僧官们又已经提前搭起了帐篷并且列队迎接我。他们给我端来茶和米饭,那两位住持向我进献了哈达和身语意像。接着队伍继续向前,当甘丹的僧众快要到达Chugo上游支流时萨济寺和江孜寺扎仓的僧人们已经列队,仿佛形成一条金色的念珠。到达Chugo后我下了马,坐在轿床上,脚下一块褐紫红色地毯面朝寺庙方向。在做了3次大礼拜后,我按照Ngaram Dampa教我的方法举行了传统仪式,包括进献朵玛时祝愿吉祥。
接着,护送队伍在前头奉香,来到Dokang 康村,这时只见一队喇嘛和官员、扎仓及康村还有向我献了哈达还有觉悟身语意像。然后,我的康村奉送了茶叶和米饭还有炸饼干以及其他食物给列队的人,以示隆重庆祝。两名哲学学僧还进行了公开辩论。
迎接仪式结束后队伍就散了,我们便上了康村的上层。许多官员和个人向我进献了觉悟身语意像还有米饭和哈达等。随后我走到阳台上。我在Chuzang的时候总是会想象甘丹那宽大的庭院里举行的大型辩论会是什么样子,而当我从阳台上看去时,它完全与我想象的一样。
有一天甘丹赤巴的一位代表把我带到第三任Tsemön Ling仁波切 Lozang Tänpay Gyältsän面前,接着那位康村上师又把我带到甘丹萨济寺住持Pukang Lozang Kyenrab面前、按照习俗第一次向他介绍我。后来,我在一个吉庆场合散发供品以示崇敬。有一次,有位上师正在传法时我邀请Tri 仁波切 Tsemön Lingpa和他的随从们去Dokang康村,并且向他进献了哈达和觉悟身语意像。
嘉瓦仁波切的代表送给我茶叶和一只银印、Kapse(形状似中国的麻花卷)堆了五层高,还扎了一条福绳。接着,僧官、康村来的一群又一群人还有亲戚们为我举行了复杂的吉庆欢迎仪式。帕绷喀金刚持还仁慈地派一名侍者送来吉祥哈达和许多锦缎,足够做几件法袍。
当我第一次走进甘丹萨济寺的法殿Legshä Kundrog Ling,人们按照Ngaram Dampa亲口所作的吩咐,像katora(碗)之类的盆子装得满满地,都快要漫出来了,前来的僧人们都分得一碗。从早上直到夜里我们都给僧人和民众们、还有法殿里的人倒一种特制的茶。此时我已经能够凭借记忆念诵绝大多数经文,只有住持撰写的献给本派的祈祷文和晚课结束时举行的chasum choga Three Part Ritual没有记住。
有一天,我听说前任政府官员(Kazur)Shädrapa 要来我的住所,于是我匆匆赶回,在住所突然见到他。他身材矮胖,头发稀疏,扎成几缕辫子,穿着淡蓝色锦缎秋巴(chupa),显得威风凛凛。他给我进献了哈达和奖品。由于自己年轻,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不作声。Ngaram Dampa 和Shädrapa是老熟人,俩人细谈着过去的事情。最后,Shädrapa 给我提了许多建议,让我特别要坚持学习,因为我”是最优秀的,就像所有鸡蛋中的一只金蛋,就像噶当寺的金顶珍宝!”Shädrapa是噶当寺的上师,当时是该寺非比寻常的年长檀越,特别是Dokang康村的首要施主。后来,他担任政府大臣,与嘉瓦仁波切来到噶当寺的时候,他们还来看我。
第13世嘉瓦仁波切再世时,Shädrapa Päljor Dorje(这是人们对他的称呼)还有另外3位(Zhölkangpa、Changkyimpa 和Horkangpa)担任噶伦4大臣。虽然嘉瓦仁波切无疑有各种理由,那些理由不是我们未能觉悟的头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在常人看来,他好像是受了一两个侍从分裂的言论所影响。他颁布了严格的敕令,说西藏议会不能履行其政治责任,还把那4位大臣软禁在罗布林卡宫里。
后来,Horkangpa成功逃脱,并在Kyichu自杀。其他3位大臣Shädrapa、 Zhölkangpa及Changkyimpa都遭到免职,回到家乡,但Shädrapa 必须留在Kongpo Orong,以示惩罚。后来,Chushur发生了来自前藏的英国军队的激战,嘉瓦仁波切突然动身前去中国和蒙古。他不在期间,名为Amban Krangtarin 的中国大臣来到拉萨,给Shädrapa 写了封信,坚决要求他来拉萨,到政府供职。于是,Shädrapa 从Kongpo 回来,Amban把甘丹的土地都交给他打理。当时Shädrapa态度坚决地对那位Amban说:”我是嘉瓦仁波切惩处并且驱逐过的人!我回来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违反了嘉瓦仁波切的命令!我还是继续当under Shädra”。根据旧的手稿如杰宗喀巴的传记记载,原先用的是”Sharahor”这个封号,后来,大约从Shädra Desi的时候起,人们更喜欢用under Shädra这一称号。总之,从大士杰宗喀巴尊者的那位檀越开始,每日由under Shädra举行内供并保留杰宗喀巴 研究过的许多重要圣物如甘珠尔,似乎成了甘丹Chögyäl家的传统。
此后不久,嘉瓦仁波切从中国发出明确指示,让Shädrapa、Zhölkangpa 和Changkyimpa 恢复大臣职位,他们自此一直担任此职,直到身故。
夏季闭关结束后,我们离开甘丹,从Marlam Dechen Gongko寓所出发,到了Karab Shänka前方的一片原野。当时我们已经备好午餐,于是便停留了一会。接着,我们在Dechen Sang Ngag Kar 拉章呆了一天,期间感受到了Dechen Lamo Tse的居民还有其他人的仁慈好客,便与他们结下了吉祥佛缘。
夏季闭关后,Marlam贡塘佛法庆典的时间快到了,Jar Rag的原野里扎了一顶大聚会帐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一边稍事休息,一边观看正在上演的戏剧,开始演的是佛陀本生故事。因为我是第一次观看戏剧表演,深深被它吸引,想多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继续行程,傍晚到达拉萨。
到达拉萨后,我必须与嘉瓦仁波切进行首次晋见,可由于他还没有从中国和蒙古返回,我按照传统去拜见他寓所的大法座。 我还首次晋见了摄政王甘丹赤苏Lozang Gyältsän仁波切,他当时住在拉萨须弥扎仓的上一层。
我们到达Chuzang闭关处后,在我们寓所外的庭院里扎起一座大会聚帐篷。为了纪念我到达甘丹的吉祥时刻,帕绷喀金刚持到场,Dromto Geshe仁波切和闭关禅修者Gelang Jiyo主持了两天的庆祝宴席。Demo仁波切和我在一边扎了一顶小帐篷供我们自己的人使用,大家在聚会上很高兴。
Ngaram Dampa请求帕绷喀金刚持做文殊教派的所有随许灌顶。我从来没有受获过Anutaratantra(《殊胜无上密》)(如怖畏金刚)灌顶,可金刚持喇嘛为了吉祥,破了一回例,给我做了所有的随许灌顶。虽然我年纪轻,不能理解他教授的其他内容,可他做宗喀巴法王随许灌顶时,我理解了他讲的举行随许灌顶故事的含义,当时没有准备棍首手形,于是用一根管子一头插一只饺子代替。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受获宗喀巴法王随许灌顶时不停地重复这样的话:”……我将遵行”,说了许多次。
还有一天,应Ngaram Dampa的请求和督促,为了吉祥,帕绷喀金刚持来到我们的僧寮,教我们如何画消灾火供、增益火供和降伏火供炉。我们稍微弄混了灌顶火供炉的线条,他就会立刻纠正。
正如前文所说,金刚持喇嘛为了佛法吉祥,破例给我做了一轮文殊随许灌顶。可我觉得由于自己当时的年龄关系,没有充分理解。因此,在我21岁时,再次由他全部做了一次。
接着,Ngaram Dampa和Tzöpa Chizur共同决定需要给我派一位上师教我著名的诸论。他们编写了一份甘丹萨济寺扎仓大上师的名单,让帕绷喀金刚持和嘉钦多杰雄登作出指示。两位上师一致认为,Pukang Nangzang的Lozang Tsultrim是一位善师,于是便请他从甘丹寺来。他那一年与Dosam Nyitso Trinle一道来到Chuzang闭关处。一日,天象大吉,举行了一场简单的仪式:我进献了茶和米饭,哈达等等。随后他便开始授课。他先是对“热突寺话题集(Ratö Collected Topics)”开头的礼敬辞进行阐释。由于我已经记住了《现观庄严论》的全部和《入中论》的一大半,这位至尊上师还对这些进行了考察,对我记忆的成果十分欢喜。
举行供奉的时候,Ratreng地区来的舞者表演了及其狂野的鹿舞和牦牛舞:只见舞者们单脚着地,前后左右漫无规律地飞旋。当时我模仿他们的样子飞舞起来,手里拿着一盏照得很亮的陶制油灯。我正在那些塑像跟前舞动,突然有一些火星蹦出油灯。当时的情景很吓人,因为那是我拜师的第一天,没有人责备我什么的。
从此以后我的圣师就与我们常住在一起。那一年的冬季法会,我们去了甘丹寺,他开始教我写作、数学和辩经,方法是提出一些话题(如在话题集的起步阶段论述色彩),然后循序渐进,通过诸如”教量确定”、孤离设别等等话题,学完话题集的初学、中级和高级各阶段的题目。我就是要这样经历四年的学习阶段的。
我八岁的时候,应甘丹的时轮金刚仪式僧们要求,多闻而且证悟的大士甘丹寺色贡寺金刚持Ngawang Tsultrim Döndän Pälzangpo在甘丹寺的白色大会堂进行《略本时轮密续》大灌顶,包括准备时间一共举行了3天。我非常幸运地向那神圣优雅的大士鞠躬,并把一朵红色的金波萝花献在他的脚下,然后与成排的新戒一同受戒。那天人太多,巨大的会堂也装不下,有人坐在门道里、还有各个地方。我坐在曼陀罗跟前,紧跟在Dräpung Gomang Kyabje Kangsar仁波切 身后。
瓶灌灌顶仪式(vase initiation)举行的时候,大喇嘛对我进行新戒沐浴,把我放在曼陀罗的布画上面,并且也许是出于节庆的目的,把安膳那混和蜂蜜然后递给我。那味道实在是好极了,我把它喝得一滴不剩!有些Tsenam的时轮金刚僧身穿舞袍,手拿花瓶,吟唱着曲调什么的;那景象真是非同寻常。
那位金刚手所说的佛法十分博大精深,他有时候会喊出或者说出一些批评或者嘲讽的话。我年纪太小,授戒时所用的那些象征性语言有些我根本听不懂。第二天,他安慰所有受戒的新戒,说没有必要怀疑自己已经得到了威力,说那就像以前的大上师拍打新戒的脸来让他们熟脫一样;即使像我这样的另类,也凭借付嘱自己的威力,对于自己已经打上特殊印记的想法绝无怀疑。
我9岁时,我们扎仓的戒律师让我们背诵本派的经文,当时要在会众中间背诵,以便获得尊贵的称号—— Kachu:“学习十经的人”。我一点也不害怕、毫不犹豫背诵雷谢宁波(Legshe Nyingpo)前两页的经句,大家都赞扬我,说我这么小能背得出很好。我得到扎仓 和Mitsän 的噶举称号后,向大家广致敬意。
Dechen Balam一位牧民的10岁儿子成了我的家徒和玩伴。此后在他66年的生涯当中,就像《Laying of the Stalks Sutra》当中所说的那样,“充当一条船、一辆车、一座金刚山”,他作为随侍对我照顾得很好,他的心非常善良。
那一年晚些时候,13世嘉瓦仁波切结束了中国和蒙古之行回到西藏。前去Pänpo的甘丹Chökor寺迎接他的有甘丹Tri 仁波切、甘丹萨济寺和江孜寺扎仓的神谕等、西藏中部地区甘丹萨济寺和江孜寺的住持们、喇嘛、杜固和官员。大家为他举行了欢快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也去了,迎接他的时候第一次能够亲眼目睹他的佛颜——那是一尊菩萨的金色面容,带有功德圆满的光辉圣迹——真是三生有幸。
接着,那些喇嘛、杜固和官员们包括Tri仁波切都动身去了拉萨,那里还要举行欢迎仪式。我当时想去拉萨并且正如Tzöpa Tzongzur 所希望的那样离开Pänpo,又回到甘丹寺。
我10岁的时候是铁狗年,就在大法会期间,第10代Kundeling Tatsag Thubten Kälzang Tänpay Drönme 仁波切要取得格西学位。于是,按照传统做法,嘉瓦仁波切和他的随员们受邀到达该寺。同样,Amdo Tashikyil 的第4世Kunkyen Jamyang Zhepa Kälzang Thubten Wangchug 也受到了邀请。
人人都十分兴奋,无论是僧人还是在家人都忙着准备嘉瓦仁波切一行人马的到来。法会正在上第一道茶的时候,庞大的中国lu’uchun部队突然到了,开始炮轰拉萨东面的Tälpung Gang,炸死了几个西藏人和大法会总持Tsedrön Jamyang Gyältsän;Punkang Gung Tashi Dorje等人也被炮弹炸伤。这个时候人心惶惶。
那天夜里嘉瓦仁波切和一些重要的随员悄悄地通过Norbulingka宫离开布达拉宫去印度。中国人如驻西藏代表Amban Län等派了一大群分遣队员追赶他。但在Chänsäl Namgang峡谷上的铁桥边,Tsarong Dazang Dradul(他此时已经入赘Tsarong家)和其他几个志愿者拦住了中国军队,并且让他们撤了回去。
那一年Yongzin Lozang Tsultrim也参加了格西拉让巴的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取得格西拉让巴学位。
仿佛由于伟大的嘉瓦仁波切从中国和蒙古返回而获得了新生,西藏政府首次铸造了一张藏(sang)钞和一枚叫Thubten Sertam的硬币,还在法会上给每名比丘三枚银币和一块khatak eraser布。Kundeling 拉章和Jamzhä 拉章又给每名僧人5枚和3枚银币。
法会期间中国人尽其所能诋毁和羞辱僧人们。他们从在庭院阳台的屋顶上,双腿伸开来,抽烟并且把烟蒂扔到会众当中。Tri 仁波切 在举行法会的庭院讲经,他们就在门前列队前行,还一边敲锣打鼓。
那年夏天我们去Sangpu举行法会,除了我学习tsänyi逻辑推理外,Ngaram Dampa还在庭院的阳台之间教授我和我导师星象学。开始我们在地上练习写乘法表,渐渐开始学习nga dü(the five-fold summary)、5大行星zhag sum(the three-fold division of days)和星象学几乎所有的星象图,先是在tsi zhong盆里把图画出来,然后擦掉。我伸出一根手指头画,对学习这些东西非常兴奋,可我年岁小,后来又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佛法和推理上,因此虽然记了学了许多东西,还是没有提起多大兴趣,最后还是把它丢到一边。因此,当时所学到的星象学的知识,很久以前就遗忘殆尽了。
我在Sangpu参加夏季法会时,Amdo Jamyang Zhäpa来Sangpu朝拜。由于当时中国人(比如住在拉萨的驻藏大臣)高度重视Jamyang Zhäpa 仁波切,仁波切的侍从们提前到来作准备。他们对Sangpu的人又是威胁又是拳打脚踢。当地一些居士税务官(比如我们住所的主人)只好逃走,在Sangpu前面的树林里躲了两三天。Jamyang Zhäpa仁波切在Sangpu呆了一天。第二天他离开之前,有10组Sangpu的喇嘛聚集在庙里,他给每名喇嘛发了半tam藏币。接见了僧众之后,他动身返回拉萨。他年纪很大,白色的长胡子,身穿黄色dhagogtse锦袍。
许多人比如拉萨市民称他”汉人喇嘛”并且贬低他,因此我对他没有多大的信仰。可是,后来我回想这个问题,除了他来的时候正好和汉人同时以外,他没有任何过错。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合格的好喇嘛。
那年秋天,西藏中部和后藏地区流行天花,于是我长期呆在甘丹做闭关。帕绷喀金刚持小心翼翼地从Chuzang闭关处把明妃一切母(Vishvamata)的仪轨和西藏宗教仪式微型绘画Tsakli拿来,于是我们念了10万次明妃一切母密咒修行,还有10万次白度母长生密咒修行和10万次缘悲经密咒修行,这些我都是同我的圣师一同念的。
当时不像现在有医治或预防天花的药。光是甘丹寺就死了许多僧人,因为前面的死尸还没有运走,连举行天葬的停尸房都没有了。我那一年也得了天花,脸上和四肢长了许多脓包。我虽然病了许多天,可我听了金刚持的建议,不停地诵读心咒,主要由于这个原因,特别是我的圣师连续不断、通宵达旦地悉心照料,我终于痊愈了,能去看冬季法会的辩论。天花肆虐最厉害的时候,不知道是做梦,还是出现了幻觉,我觉得自己来到Nyagrong关口,几个在我上方的僧人向我召唤:“亲爱的小孩来吧!咱们一道去兜率净土!”仿佛即使我在那个时候死去,也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还产生了这样的幻觉:有一种动物像猫或者狗呆在我膝盖上,一个妇人走过来把它抓走了。我后来得知我在我妹妹Jampäl Chötso后面出生的弟弟在我产生幻觉的那天死在贡唐——他曾被认定为是Lelung杜固的转世。仿佛他代我而去了。
我得天花的时候,Pukang寺住持Lozang Kyenrab建议我的圣尊师Gän Yongzin Chog先是用酸角(tamarind pine)治。后来,脓疱化脓的时候,又让他用佛香的白烟治。有一天那些脓疱瘪了,开始进到里面。这时情况变得很危急,我的圣师十分担心。他问那位Pukang的住持是怎么想的。住持说拿一块猪肉煮熟了,让我吃几口肥肉。我师傅照着做了。第二天,就在那些脓疱瘪的地方,又长出了新的脓疱,就像塔上又长出了一层。于是,我慢慢地好了起来。
我弟弟死于天花后,留下的只有我母亲和她女儿Jampäl Chötso。住在贡塘的那两位喇嘛Apo and Ane Yangtzom 继续像仇人一样对待她们,她们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Tzöpa Legshä Gyatso把她们送到拉章一位成员Dechen Karab Ogong的家里。Dechen Karab Ogong的父亲Tänzin Zangpo和孙子Döndrub住在那里。
我11岁的时候,Deyang Tsänzhab Nyäldra的转世Tänzin Trinlä Özer 仁波切把拉萨须弥山东云堂的Domä 版Tukän Chökyi Nyima 选集14卷读本经文集送给我。
每年,Tängyäling 拉章都会盛情邀请我们去参加第穆(Demo)的羌姆(cham,金刚法舞)。第穆羌姆舞上方观赏区坐着第穆仁波切。他右边坐着Derlo Sempa、Dagyab Chungtsang、Tsangpa Känchän、我还有第穆仁波切的导师。他左边坐着各色汉人大臣如冷(Len)安班等。级别最高的居士政府官员Kashag Zhab Pa等则在两边住所所在的最高观赏区。其余的政府官员随员则在阳台下面屋顶上所搭的帐篷里。
汉人抽烟冒出的烟雾充满了观赏区。看到一个叫Tzasa Chöjang Dradül-lag 的人似乎非常乐于向汉人献媚,我十分不快。吉祥天母玛佐嘉摩舞的主舞和伴舞们快要结束的时候,12天女之一(Tänma)、饰演Kongtsün Demo的演员不仅在经过装饰堂皇的宽大国道时面朝地面摔倒,而且汉人安班还给每人都献了哈达。总之,拉萨人都觉得这些是非常不详之兆。第二年,与汉人军队开战造成丹吉林寺化为废墟。
那一年,过完夏季闭关、我还没离开拉萨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场起义。就连拉萨都在佛陀天降日(Lhabab Duchen)发生了拉萨的汉人新旧派系之间的战斗,许多汉人彼此杀死了一些对方的人。他们还相互把对方逼到拉萨一些市民家中,还抢夺了马匹和驴。由于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打斗,我和圣师在拉萨的Trokang寺租了一间小房间,在那里住了许多日子。
当时,那位名叫Län的驻藏大臣只好离开拉萨,躲到哲蚌寺里。
宗喀巴圆寂纪念日(甘丹五供节)时,我们去了甘丹寺,Ngaram Dampa教我和老师画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怖畏金刚和Künrig的曼陀罗,详细讲解它们的颜色、仪式知识等。我们在甘丹寺的房间墙上非常勤奋地练习。Gän仁波切和我画了一些完整的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曼陀罗。最后出来的效果很好。当时康村寺的上室正在翻新。
冬课期间我进了一个新班,开始修习《帕尔钦》(Parchin)、《波罗蜜多》、《诸波罗蜜》等。当时拉萨地区藏汉之间发生冲突,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我12岁的时候,和Gän仁波切还有Ngaram Dampa都没有参加大法会,而是呆在甘丹寺。那一年政府从每个寺庙抽调僧众,组成1000名卫兵,因此给大法会上的僧人们做了大供奉。
当年2月,汉人突然攻打色拉寺。西藏社群发布命令,从甘丹调集200名僧人火速支援色拉寺。他们扎上皮带,带上一些原先在各处忿怒明王塔婆室安防的前膛枪、刀和矛。有些僧人穿的衣服非僧非俗。长袍外面罩上藏民服,脚穿皮僧鞋,头上等处扎着各种颜色的藏经罩布。他们出发的时候,那景象简直让人目瞪口呆。他们到达色拉寺后,与一些年长的僧人见面并且互碰额头。老僧人们泪流满面,告诉他们说这所先前著名大寺院的僧伽已经完了。他们说有些僧人在棍棒的头上绑上菜刀,跑走的时候猫着腰说:“那些汉人在哪儿?我要去杀了他们!”。
后来,西藏政府军和色拉寺还有甘丹寺的僧人们联合起把汉人赶出了色拉寺,一直赶到拉萨南面的Lhogyu。有些在家学徒,比如我的仆从Lhabu和8个在甘丹寺念甘珠尔经(Kangyur)的僧人只好在汉人的统治下生活了不到1个月。他们被迫在Lhogyu到处干活,缺衣少食。汉人强迫他么在山沟里挖土和石头,然后搬运土和石头构筑掩体。有些人(比如Lhabu)因为搬运土石背上都长了脓疮,但还是不让他们歇息。他们经受的危险、恐惧和痛苦真是难以想象。
那一年,由于正在开战,我们不能在Sangpu的夏季闭关会上举行荟供。我的班上有一名Pukang Yara家的男孩,他家在Markham Chashäl地区的Zadru寺、Kapo Ze村,名叫Ngawang Lozang。他非常聪明,学习好得不得了。他性格非常和善,成了Gän 仁波切的弟子。从那一年起直到他获得格西学位为止,都一直是和我搭伴讨论佛法。有个Dokang来的弟子名叫Lozang Chödrag,他很优秀,到寺里来本来是要在这段时间参加夏季闭关的,住在康村的上寮舍。我们在会众面前举行公开辩论的时候对《波罗蜜多》进行探讨和辩论。开始是《总释Chishä》当中对佛法的礼敬,接着进行探讨辩论,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诡辩的情况。Tzöpa Tzongzur Legshä Gyatso非常慷慨大方,承担了例行传统大供奉的花销。
拉萨爆发激战的时候,迫击炮的轰鸣声可以在甘丹 Nyagrong 的关口听到。那年,遵照最高政府的命令,甘丹色贡金刚持来到甘丹寺,在羊八井的法王佛坛前举行了绝密法王威怒“毒黑山”朵玛仪式,还把祆朵玛(zor torma)扔到集市大棚的顶上。那天僧人们大声诵读色钦仪轨,我在Dokang的上室都能听见。当天还举行了拉姆和马头明王(Hayagriva)朵玛仪式以除害,还有si nän即驱除”si’”鬼仪式,以及其他一些威怒仪式,一个接着一个,连续进行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那是铁狗年初,有一天嘉瓦仁波切从拉萨来。自愿跟随他的,有一位汉人高级将领和小昭寺住持Ramoche Gyälgo Donggi Chötzä。他举行了si nän 仪式,地点是Drag Go Che Par Nang即”大石头外门”,甚至还愤怒地把士兵(包括甘丹寺的士兵)杀死的人的头和肢体作为祭品。每次扔多玛,Serkong 金刚持都想模仿那个动作、跳着羌母(cham)舞步,还跳错了,失去了平衡。金刚持过早地谢了顶,有一会我孩子气地想:“他的帽子要是掉了,那就好看了!”
那年夏季闭关结尾的时候,拉萨附近的战事还没有解决,于是我们在Dechen Lamo Tsezhi的准闭关处呆了两个多月。Gän 仁波切让我背诵Legshä Nyingpo,起初在一天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假装在背诵,实际上是在挑一些特别的词、杂乱无章地背诵。让我背出来的时候,不管让我看的是哪个部分都一样,开始、向前、向后,我开始从书页的背面读,就这样读了大约15分钟。我作弊被发现之后,不仅遭到责备,而且受到一顿鞭打。我只好从头开始背诵,坚持下来,记住了大概70页,还有班禅所著“波罗密多概述(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Paramitas)”当中关于“20僧伽”的第4章。
当时,由于我天资很高,Gän 仁波切希望我能大大提高记忆效果,可由于我缺乏毅力,Gän 仁波切经常督促我责备我,好让我顺从。我身上长了许多跳蚤。有一天朋友Yöntän-lag帮我一起把床具抖了抖,抖出来的跳蚤装满了一只杯子!
那年9月我随Gän和Ngaram Dampa去了贡塘向我的出生护法祷告。贡塘拉章的管理人、我舅舅Zhangpo Jamyang Gyatso让我们住在宽大的上房,我们呆了几天,每天的饭食都按时从舅舅的房里送来。另外,正如我前文所说,有一位在贡塘的,名叫Ane Yangtzom的热播不相信我是贡塘喇嘛真正的转世。由于当时他管伙食,要是由他来决定的话,一天也不会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 Kuntse Gomag Tsipon Rinwang和他妻子(也就是我姐姐)从拉萨来到贡塘,呆了大概一个星期。
有一天他们过来与Ngaram Dampa见面,给我们供养茶和接连4顿饭!可是,Ane Yangtzom对我们不理不睬,就像我们是木头,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不光那时候,而且直到我获得格西学位时为止。我们每当从拉萨到甘丹寺经过贡塘时,都在我舅舅Gyatso在Chökor Ling的家里,我更没有想过要去贡塘拉章。
由于拉萨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宗喀巴节的当天晚上我们从Dechen回到甘丹寺,虽然《波罗蜜多》学习班已经结束,我还是坚持一个接一个地学习其中的论题,开始是森结(sem kye)、菩提心、当那(dam ngag)、教诫,等等。
冬课结束后我们去了拉萨,12月16日,第13世嘉瓦仁波切从印度回到拉萨,政府在Kyitsäl Luding举行了欢迎仪式。三大寺庙的喇嘛和杜固们都去朝见他。
我13岁的时候是水牛年,拉萨大法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按照Ngaram Dampa的旨意邀请Tsedrung Zhabzur Sampel- lag到我的僧房,我、Lhabu和Tzong Legshä的侄子三个人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写字。同时,我们在边上记忆、背诵和修习逻辑推理。
荟供法会结束后,我们与Gän 仁波切还有Ngawang Lozang去了哲蚌寺,接受整部《甘珠尔》——这是翻译成藏文的佛法大成——还有丹珠尔,由Gomang Hardong僧房的Kyabdag Kagyurwa Jetsun Lozang Döndän Pälzangpo传授,还受获了许多其他的读诵经传,如《嘛呢卡布经》和《父子噶当经(Father and Son Teachings of the Kadam)》等; 总共花了3个多月。仁波切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有人睡着了,交头接耳,记笔记或者什么的,即使动作细微,常人难以察觉,他都会停下来;因此教学秩序井然。
哲蚌寺的教学结束后,我们转到甘丹寺,在随后的夏秋两季,都听Gän仁波切的教诫,我顽强地学习《波罗蜜多》,同佛法学习伙伴Ngawang Lozang从“20僧伽”一章开始,一直学到第3章。我们学习得无比刻苦,在当年的冬课期间,就跳级到了高年级学的《波罗蜜多》第8章,同时还在冬课期间学习第4章。
我14岁的时候是木虎年。大法会结尾的时候,应Tatsag Hotogtu仁波切尊者的要求,在拉萨的昆德林(Kundeling)云堂,哲蚌寺Gomang Büldü金刚持Jetsun Lozang Yeshe Tänpay Gyältsän的无数加行,他是千百家族的金刚萨埵王。他把众生的心灵与四合体的道果合为一体。仪式预演准备的日子里,用涂漆的曼陀罗举行了大法会。我们还接受了关于善友派观世音瑜伽(Mitra-system Avalokitesvara yoga)和Nyän Tsembupa派观世音瑜伽的三要点。金刚持作了博大精深的教诫,说明修习法的时候鞭辟入里。
我年纪还小,因此他对深奥无边的经文和密续要点所作的解释不合我的脑筯,但我在法会期间对于让我们观想的要点,却能理解其中的几乎全部。因为这个,知道今天,当时听到的解说和对于那位喇嘛仁波切的表情都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与乡村那些长老受获的一套又一套、成百上千的灌输却不得其解的情形相比,我年纪虽小却理解得相当不错。
为了学习通学科的目的,我当时从《波罗蜜多》第5章开始学,在夏季闭关期间同一位甘丹 江孜寺 Gobo的僧人一起学习,他是个十分有名的优秀学僧。我们在僧众面前辩论《波罗蜜多》第8章,因为辩论得很好,那些博士无法嘲笑、也无法觉得尴尬。邀请Chogtsung Trichen金刚持 Kyenrab Yöntän Gyatso Pälzangpo担任会众领班时,我有幸以传统方式向会众作供奉。自始至终大事小事都十分顺利。冬课期间我升到Madyamaka班。
我15岁时是木兔年。6月17日,按照甘丹江孜寺 Tsawa戒律师Zurpa Yeshe-la的要求,第88任甘丹赤巴Trichen Kyenrab Yöntän Gyatso Pälzangpo在甘丹Yangpachän寺举行带有多日预演的45次大灌顶。Kyabchog Büldü 金刚持、五论师王哲蚌寺 Lubum Geshe Sherab Gyatso 仁波切与600多位僧伽(包括著名而且博学的喇嘛、杜固和格西)都受获了吉祥福会。Tülzhug期间,广泛进行了六转轮胜乐金刚造行及灌顶。我接过明王法衣(如六个骨庄严具)穿在身上,大家手持华盖、胜幡等绕曼陀罗而行,还将弟子供奉给明王,等等。所有在场的僧众都得到大公德和大福报。
在进行这些大法会期间,我有幸坐在Kyabchog Büldü金刚持身边。他是我的最好榜样,我看到他自始至终都全神贯注地静思观想,心无旁骛。由于上一年在Kundeling举行的大法会期间仔细谛听等原因,我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不间断地进行观想。当时,我随Kyabchog Büldü 金刚持修习语法。他建议说,如果我向Geshe Sherab Gyatso 仁波切学习语法会很好。
那年我在冬课期间升到古代Madyamikas班。
我16岁时是火龙年,大法会结尾时,我和Gän 仁波切邀请哲蚌寺Gomang Lubum Geshe Sherab Gyatso授课。我们挪到Chuzang Retreat处。那位珍宝格西凭借本经语法课文和Great Situ Commentary,加上Prati Geshe的注释(该注释注重书写)用Sum-chu-pa和Tag-gyi-jug-pa的语法课文深入教授我们1个多月。
后来,他给我们的范文都是带音步的诗文,好让我们能够修习作诗。为了教授我们如何把那些字母和各种语法因素进行结合,他让我们用字母表中的字母依次做为第一个字母作诗,叫字母连环诗。尽管我是第一次作诗,但那位珍宝格西却对我所做的诗十分满意,还亲自作了一整套连环诗,以示赞扬,开头是这么说的:”凭着高超的智慧作成的这套连环诗,我心甚乐,非但说说而已……”。
那年我还在甘丹寺温习了他教授的课程,结合语法从初阶到高级阶段的所有内容,写了一首全套字母连环诗范文。语法课程结束后,我们挪Sangpu进行夏季闭关。
由于我所绘的画不大出错,夏季闭关期间,我在课程辩论对手Ngawang Lozang的房间里、在一张招贴画上画了由六长生像和四佳友像构成的图、每个像下面都配了一首诗。我在四佳友像下面配的诗是这样说的:
“仙湖称颂五论师无边佛法,
妙音天女携天鹅共襄盛事。”
由于此诗画显得过于夸耀而无实质内容,Gän Sherab仁波切以一种诙谐的语气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加以责备:
“ignoramus of the five dregs如我者,竟可称颂为五论广上师,
可五论大师驳斥我所论之语,我不敢声称自己懂得五论!
开些玩笑,让你熟知幽默:儿子出世,块头比母亲还大!
匆匆写下这些,尖锐地提醒你,好让你卓越的公德,更加无与伦比!”
那年冬课期间我升到轮藏班,除了按照Gän仁波切的教导主要根据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弟子们、以及班禅索南扎巴的著述学习了《波罗蜜多》和《中观论》等经文,还尽我所能,学习了Je Gendun Drub、Kunkyen Jamyang Zhepa和Jetsun Chökyi Gyältsän的经论。
我17岁时是火蛇年,哲蚌寺Hardong 密续学院举行完法会, Büldü金刚持进行Gandhapa五尊胜乐金刚大灌顶和Rinjung Gyatsa随许灌顶,我和Gän仁波切都参加了。我们睡在Lubum 康村上方Gän Sherab仁波切的僧寮里。由于Ngaram Dampa在门朗期间和后来身体微有不适,我动身前往哲蚌寺时,他来给我送行,对我进行了大量通俗诚恳的心要教诫还有诚挚的建议。我离开的时候痛哭失声,因想到这可能是我们的永别而十分伤感。
2月17日在哲蚌寺聆听佛法时,我们得知Ngaram Dampa已经圆寂,大家都感到无比悲痛。Ngaram Dampa于第14个甲子的木龙年出生于Barkam县Sho, Tar和Lho的Ala Ngödro Kä村,属于Ayig
Thango家族。他起初入了Ayig寺,修习读诵。后来他去了西藏中部,进了哲蚌寺Gungru 康村,几年后进入上密院,精修密续仪式,后来成了密续仪式方面的大师,精通沙曼陀罗(sand mandala)、朵玛等的制作。他顶礼膜拜过许多适格上师,其中有大博士、瑜伽师Tatsag Yongzin Gedun Gyatso、Kagyurwa Lhotrul Ngawang Kyenrab Tänpay Wangchug; Gomang Känchen Kyenrab Tänpa Chöpel; Gungtrul仁波切 Kyenrab Päldän Tänpay Nyima及前任Yongzin Ling仁波切Lozang Lungtog Tänzin Trinlä等,还受过无数灌顶、经传和口授。他还精通受到印度与中国影响的西藏黑、白占星法。
有一段时间,他听从Yongzin Ling 仁波切的建议,去自己家乡进行Vajra Bhairava大闭关,他动作精确,准备、进行与结束都十分完整到位。然后他去了西藏中部,入了密院,当了几年的Amdo Kangtsan上师,非常无私地对密院做了奉献。他给我讲了许多生平事迹,多得在这里说不完。
后来,前任甘丹赤巴Lozang Tsultrim Päldän担任上密院主持;他担当执事,直到担任金法座,而且在担任甘丹赤巴的5年间也是如此。与后来的情况不同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某个喇嘛当上密院住持或甘丹赤巴后,照管僧伽贡品开支和担任住持期间其他供奉开支的责任由拉章承担,而且责任行使时毫无障碍。礼敬僧伽的仪式也是十分繁复,恭敬有加,不是漫不经心或者草草了事。
前任甘丹赤巴去世后,继续伺奉他的是Ngaram Dampa,他负责一切事物,比如为这位喇嘛的去世举行供奉,火化,在甘丹寺Yangpachen为他造舍利塔等。
认定我为杜固之后,他与前任甘丹赤巴的侄子甘丹Chizur Legshä Gyatso负起一切照料与教导的责任,还担任我的识字老师直到他将要去世时为止。他对我特别关切,就像我的父亲。就像我说的那样,他教我识字、读诵、制作仪式推算图、进行密经曼陀罗的度量和上色,还有制造立体密经曼陀罗等。不用多说,他还在密院教我kangso护法仪式、如何举行仪式、怎样拿曼陀罗,等等。
他教我制作16角威怒朵玛、怎样堆垛9 yug gu、抛掷朵玛,甚至如何制作法王chu ma朵玛,如何制作16套四yug gu ,以及为什么要做4套供奉等。简言之,关于制作朵玛的一切知识,以及制作方法的原因,都无一遗漏。
他教我每一种密续修习的程序,聚集和遣散会众的方法,指导主持仪式的各种方法等都无一遗漏,而且教的是亲身体验过的最为纯粹传统的修习方法,从无以世俗的“推销货物”之心,并且他总是在这方面对我进行教导,后来我受获格西学位、全力修习密续时,我不用像许多格西那样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初习密续,而是对密续修习耳熟能详。不仅如此,学习Drag Yerpa Cave教义的时候,我已经会画曼陀罗的主干线条,轻松通过了住持和上师所出的有关曼陀罗维度的试题,年轻的学匠在修习方面有疑问可以向我提出以解惑。所有这一切皆因Ngaram Dampa 的恩慈,我对他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就以某一天的业行为例,我们凌晨金鸡报晓时即起洗簌准备。回忆当天的吉兆后,我们诵读经文以赐福我们的言语和”倍乘”经文。
接着,我们跟随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瑜伽法诵读几百遍缘悲经,几百遍皈依祈请文,怖畏金刚孤雄法本,同时念诵一圈念珠的百字明咒。他还念诵许多遍怖畏心咒,而且轻松缓慢地念诵;我们念完时,是在供完多玛后、举行法王仪式开始时,他会继续进行完整全面的法王仪式和观想、圆满和忏悔长短仪式与赞颂,同时,他会让我行100遍水钵供奉。为了我,他会作长生白度母修行,用几百个手印的朵玛、surupa和sur火食供奉Torma Shaka Tubma。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才用茶并进一些早餐。
然后他会检查我的读经和诵法情况。到了适合教诫新的佛法时他会进行全面的沐浴,同时念诵Jorcho前修习文、Thubtän Lhunpo’i Tzegyän,制作许多曼陀罗贡品以为资粮,持诵忏悔文(Confession of Downfalls)且做几百个大礼拜。
接着,他会进行马头明王法本秘传独修法,每天念诵5000遍根本经,从不间断,同时在Chuzang的辩论庭院当中稍作散步,或者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去检查下我们做的效果。
中午的时候,他会念诵《三宝随念经》(Three Jewels Recollection Sutra),然后用午餐。扔出手印朵玛后,他获举行金刚水火供。供养出第一部分后,他会印上几百个小佛像,同时念诵Choying Taläma以向与大黑天密不可分的上师供奉。他还会念诵一圈念珠的三昧耶金刚心咒、香巴拉祈祷文,然后为了我而念诵《十六阿罗汉祈祷文》(Prayer of the Sixteen Arhats)、《Peak Forces Ornament Dharani》和《十方驱散黑暗经》(Dispeller of Darkness of the Ten Directions Sutra)。他还念诵《密集金刚根本经》(Guyasamaja Root Tantra)全十二章、胜乐金刚根本密续第一章和整部《般若经》(Prajnaparamita Sutra)压缩版,发音无半点瑕疵。
这时他会去Chuzang Lingkor闭关处绕佛。午茶过后,为了帮我做功课,他会念诵《五尊作明佛母密心咒》(Five-Deity Secret Kurukulla)仪轨和心咒。接着,做完《Kyung Nag Meyi Putri, Black Garuda Razor of Fire》念诵和禅思,他会念大约3000遍嘛呢心咒。每天早晚,我们每人都会练习六段上师瑜伽。在每月第3天或第9天,我们会向法王进行普遍的Drugchuma朵玛供奉,每月新月、满月和第8天,Ngaram Dampa会安排我进行教敕保护沐浴,沐浴时有时用马头明王法进行,有时又用Vajravidaran法进行。
他每天念诵法要和经文时声音总是不紧不慢,清晰准确,因此我始终可以清楚地听见,我的心灵总是很宁静。他与密院行者们坐在一起时,即使是念诵密集金刚这样的内容,也能与其他僧人融为一体,十分和谐。
他在拉萨和在甘丹时,会从早上开始念诵马头明王经,然后边接着念诵,边绕lingkor。另外,虽然Ngaram Dampa没有格西和Kara的头衔,却受获过适格上师传授、内容广泛的经文和密续教诫,包括灌顶、经传和教诫。而且,正如我前文所说的那样,在三昧耶戒方面他几乎与世无争,从不以做过闭关的瑜伽大师身份示人。
即使在政治领域,他也十分明智,清楚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末梢,恪守三昧耶戒,他是个殊胜长老,智慧堪比梵天。即使他在承担重任、比如担任上密院Amdo 康村驻院上师期间,所有的密院僧俗都一致认为他比别人殊胜。就以我们的家宅为例,前任甘丹赤巴去世以后,虽然乡城当地和佛学院、内部和外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择机排斥我们,用精心策划的各种罪名指责我们,但他像群山之巅那样岿然不动,游刃有余地照管拉章,保证一切顺利。
当他接近生命的尾声、身患疾病时,每天奉持大乘戒律Sojong,只喝牛奶而不进粗粮。除了让人为火化自己的遗体而制作新力器之外,他给将要看顾火化现场的乡城 Nyitso Trinlä和Tzongzur Legshä对怎样处理自己遗体作了许多教诫。他去世前整整一年,每晚都在就寝之前禅定修习颇瓦,从而将自己的知觉像流星一样射向净土。总而言之,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完全适格的上师。火蛇年2月17日,他74高龄时去世。荟供之后,我们在哲蚌寺Hardong密院受获了Büldü金刚持住持的马头明王秘密大灌顶、Zurka Gyatsa随许灌顶、《依止上师诗50首》著述、《许愿诗20首》和密续主、次许愿。
我18岁时是土马年,Tzöpa Tzongzur Legshä Gyatso病得很严重,什么治疗方法都不能逆转病情,最终,他于3月1日圆寂。
在此期间,Chizur负责管理我们的家舍。虽然我和Gän仁波切只懂得佛經,没有管理经验,但Gän仁波切没有很多的弟子,负担不太重,Chizur突然把管理家舍的责任交给我们俩。我们核查那位执事所管理的文件和物品时,发现现有的资金不足100块银币,而且Ngaram Dampa后来还病了很长时间,每样东西都快要用完了。只剩下大概两个半桶的牛油和一、两块茶砖,所以料理他后事所需的一切都必需向别家借用。
Chizur很了解外面的世道,总是把每个人都考虑到,因此每件事都让他管理得仅仅有条。当时我们欠了许都债务,他把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那些债务不仅没有偿还,而且每笔(比如借Tseshö处的那笔)还每月都在积攒利息。我们把所有的账目都累加起来,记在一个小黑簿里,总额达到tamdo,包括为准备火化所借的6块银币等等,总债务达到300块tamdo。
当时西藏的银子总体上很稀缺,与后来中共占领西藏时相比,当时欠300块tamdo银币让我们觉得像欠了3万块那样多!债务造成异常沉重的负担。当时生计很艰难,大家对于各种开支如大麦、茶叶、布匹等的开支不断争吵。Ngaram Dampa把管理责任交给Tzongzur Legshe以后,在拉萨的水鼠年,由于与中国军队开战,Tzongzur Legshe承担了沉重的开支,没有办法归还我在举行法礼前后、参加各种考试等造成的债务。除了3个游牧家庭供养我以外,我一无所有,连巴掌大的土地都没有。虽然那3个家庭不断供养我,他们提供的供养却为所有的住户及他们的亲戚共享。就像密勒日巴尊者所说的那样:
雷霆闪电南国云,
来去太空非他处;
自生自灭别无缘。
彩虹霁月云与雾
寂灭诞生自蓝天;
自为来去无他故。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拉章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但败絮其中。我住在寺里时,除了在拉萨举行大法会的那次得到一件打了五六个补丁的罩袍和一件同样打了补丁的zän以外,一无所有。我们每天只能吃粘粑和几片素菜,所以如果没有格西考试、正式典礼或其他仪式,一到晚上似乎一切快乐都消失了。接受个人供奉、比如举行葬礼时,我会悄悄存起几块硬币,这样到拉萨时,我可以派亲随Lhabu出去几次,从一家宾馆买一些mog-mog。
有几次我们比较容易地从密院一个熟人那里弄到一些mog-mog,但只能在执事看不见的时候吃。当时钱少,吃的东西贵。我早些时候会从Yardrog牧民家里买一点干羊肉,价格是四分之一只羊3 päshag zho,后来是四分之一只羊5 päshag zho,然后偷偷地躲起来吃。说到生活条件,我们仅仅处于维持温饱状态。举行拉萨祈祷节和荟供法会期间,色拉寺和哲蚌寺的一些喇嘛和杜固衣着光鲜,让人欣羡。但那时人人日子艰难。格西Ben曾说:
从前,我的嘴找不到胃口,
现在,吃的进不了我的嘴!
就是这样,我们此生不会白受苦,只有此生受苦才是指引我们的仁慈功德导师!
那年夏季我去Sangpu进行闭关,因为甘丹萨济寺的一名僧人Dokam 康村督促,我向80位僧人僧伽诵读了《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经传。几年以前我就已经记住了论藏根本经文,但为了掌握其中的意思,我当时正在修习色拉美寺Gyälwang Choje的论藏经文,该经文非常浅显,吸取了Je Gendun Drub、首任嘉瓦仁波切的论藏著述,Tharlam Sälje,和Illuminator of the Path to Liberation等当中的内容;我当时还在深入学习Chimjam Yangpa的论藏著述;因为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习,所以对论藏8个章节当中的根本经文所作的著述,我都能随口引述几行。
当时,有位工友叫Nyagre Lodrö Chöpel 的给甘丹萨济寺住持做工,甘丹色贡金刚持称赞他是自己一名最优秀的弟子。出于对他、Gän仁波切和我的巨大关心,真妙住持Kän仁波切专门将当年(土羊年)的格西拉让巴考试提前。当时该密院还没有朵然巴格西与Lingsepa的学位,论藏也不以律藏为必修课,但为了让我学习律藏,这位住持破例将律藏班挪到夏季闭关期间。
因为我当时已经记住了色拉美寺Me Sharchen撰写的律藏概要,我在听课时背诵了根本著述的要点。就这样我在夏季闭关期间学习了律藏经文,并且按照传统做法,当着会众的面接受了律藏综合考试,同时参加了密院举行的论藏考试。重大节日期间,两所密院按年轮流举行合众护法会诵经和其他念诵活动,这一年用的是与众不同的甘丹萨济寺诵经旋律。由于我对护法会的吟诵旋律和其他吟诵旋律深有感悟,而且当时必须为一些吟诵活动写出新的、与从前的Kangso和其他吟诵旋律不同的旋律,于是,在密院一些代表的怂恿下,我想出了那些旋律,最后在经书的末页写出了曲子。
在甘丹寺举行Ngamchö的那天晚上,我在甘丹寺僧众面前接受了Dorampa说法和论辩考试。我背诵了大约30页的Drang-nge Leg-she Nying-po 和Essence of Eloquence of the Provisional and Definitive,还在大云堂和辩论庭院中接受了两天的考试,每次甘丹萨济寺和甘丹江孜寺的学匠们都向我抛出各种问题,我都能给出满意的解答而没有辱没自己的上师。
我的一个佛法学伴当时从甘丹江孜寺的Tsawa家舍受获了Dorampa学位,名叫Chödän格西,是一位殊胜的博士和仁慈的人,前任嘉瓦仁波切后来委任他为甘丹江孜寺的住持。
举行Dorampa考试那天,嘉瓦仁波切从罗布林卡宫派了一位信使骑马过来,发布一条命令,要求当年(土羊年)为取得Lharam和Tsogram 格西学位而参加公开辩论考试的学匠必须于两天之内到Norling Kälzang宫、在中午进行。于是,第二天,Gän 仁波切和我还有我们的学伴Ngawang Lozang当天经过Shätsöl到了拉萨, 次日中午到达罗布林卡的客舍。在此之前,参加Geshe 拉让巴学位考试的学匠必须由各个寺庙的住持提名,可这次来了个改变,在没有前例为依据的情况下,政府发布了拟定的考试内容。当年(我参加考试的前一年)的格西突然到罗布林卡宫参加辩论考试,各寺院的住持被召集到辩论现场,有人告诉他们,当年的格西当中似乎有人没有达到拉让巴学位水平,可因为这是辩论考试首次在罗布林卡举行,就破例保留他们的学位。
可他们没有说明是不是从第二年开始,那些达不到最优格西要求的学匠是否就会面临取消格西学位的处分。后来传来消息,说就连那些住持都收到了批评,因此辩论考试开始前两天,人们心中充满了担心和焦虑。
实际举行辩论考试是在罗布林卡宫阳光客舍,Tänpa Dargyä作为嘉宾出席现场见证辩论过程,Deyang Tsänshab 仁波切为主考。嘉瓦仁波切有时一边从他位于上方的寓所、从帘子遮蔽的门后向外观看,一边难以觉察地聆听和观察。展开辩论的学匠不得自选辩题,而是由Deyang Tsänzhab仁波切选定参照的经文或戒律作为辩题还有观点。有些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格西一边等待一边来回踱步。
尽管辩论的题目未定,但有些辩题却重复提出,然后又跳到别的辩题,仿佛一切天定,但我始终没有受到反驳;经过理论陈述后,无论我自己接受与否,都不会盲目地赞成哪一方观点,也不会被考官提出的论题弄得晕头转向。考试结束,我回到甘丹寺,一路上脑子里不停地琢磨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的4个格西学伴Dokang Samling Batar、色拉寺的Mey Pomra Ratag、色拉寺的Je Dänma 杜固和蒙古的HotogtuGomang Uchu Muchin被留在拉萨等待结果,而结果大约有一个月都没有出来。后来Hotogtu被罚了10块金币,Danma 杜固被罚5块金币、Serma Ratag和Gashar Batar各被罚了1块金币,勉强保住了格西学位。
格西 Batar的格西学位授予仪式在第二年的冬课期间举行。在11月的望时、第一次冬课期间,他在大云堂向全体会众供奉茶水和热米汤,另外给每位僧人进献两枚西藏tam币。他还在 甘丹萨济寺扎仓向每位僧人进献茶和热米汤,又向每位比丘进献一条哈达、一块毛巾、两枚甘丹甘丹颇章政权铸造的钱币和一块yang tam好运古币。
他还向全体会众进献了三尊长生天锦缎唐卡(用于大护法圆满和除悔典礼)、一付很大、带盒子的銅抜(由领诵敲打)。
他给Dokang Samling的僧众进献的供奉与给康村的相似,还在新年大会上额外给了一些供奉。对甘丹江孜寺扎仓的僧人,他每人进献了茶叶和两块白tam币。对Serkong 康村 和Samling的人,他给的供奉与给江孜寺扎仓的差不多。因此,他遵循了以前的传统做法;因为他要在萨济寺佛学院参加两天的辩论考试,还要在Dokang、Sogpa、甘丹江孜寺Lubum、 Gyälrong和Trehor 康村的庭院里参加辩论考试。甘丹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在Chötri 扎仓和Zim Kangshar扎仓举行供奉,这样至少可以防止被人遗漏。12月8日,那些拉让巴格西们在哲蚌寺从在场的嘉瓦仁波切的几位代表、一位政府官员和一位住持手中取得了名次证书。Gän Yongzin Dampa担任我们的代表,考试日期定在1月6日。
我19岁时是土羊年,将要在大法会上参加拉让巴格西考试,于是我在当年1月3号到罗布林卡宫排在人群第一排,以等候嘉瓦仁波切觐见。实际考试日期是1月6日。当时有3群僧众。我要向第一群僧众陈述5部本经,分别在上午陈述量学,在中午陈述《中论》和《波罗蜜多》,晚上陈述《律藏》和《论藏》。我必须对别人提出的诘问做出应答。不能说我在整个考试期间都保持纯洁的动机(比如出离心、菩提心等等)而没有不良、污垢的动机如恐惧、期待和自负与夸口,但我给出的答案都是直截了当的。我诚恳地做出解释,绝不不懂装懂;但尽管色拉寺和哲蚌寺的许多最优秀的学匠把论点像雪片一样砸过来,我也毫不慌张或者卡壳。7日早些时候,我在甘丹大会进献贡品,还分别在两个扎仓和向康村的僧众进献。那天,在大法会晚茶时,我向会众献茶,还向每一位在场的僧人供奉一枚tam币。
许多与我有来往的好心人都来到现场,向我进献哈达以祝贺我取得的考试成绩,Gän 仁波切和Geshe Sherab 仁波切还有许多格西、佛法学伴以及与我有来往或者认识的学匠都开心地说:“昨天的考试十分顺利!”
正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我们的家舍欠了许多债。因此,为了庆祝那尚未公布的结果,我们只好把几只八供杯、一套护法供杯还有其他一些银器、一只6英寸的gau Zeu Lhakhang金色护符盒,还有一些前任上师在世时的布匹拿去卖掉,来筹措供银、买米的钱等等,结果发现刚好够举行供奉典礼的花销。另外,东Dechen Balam供奉的牛油差不多刚好够用,我们又向别人借了一点; 就这样,我们解决了我的格西考试庆祝费用,没有增加多少债务。
大法会期间,白天从早上到中午和晚上的活动包括早茶和荟供中间的上午公开辩论、讲经还有中午和晚上的公开辩论、将相关的著述运用到各自的根本经当中等;所有这些都遵循古代的传统做法。有一个传统是在法会上扔完朵玛之后,格西们去拉萨拉章的僧房觐见嘉瓦仁波切,其中最优秀的辩手会受获奖品和名次。可是那年,因为嘉瓦仁波切正在进行大威德金刚闭关,政府人员便让我们这些格西和那两个住持在罗布林卡宫觐见。在“阳光”僧寮,Tse Kändrung Cenmo阅读了名次列表。第一名是哲蚌寺Gomang Hardong的蒙古人Borä Tuwa Thubtän Nyingpo和哲蚌洛色林寺的Minyag Tashi Tongdü。第二名是色拉杰寺Hardong的蒙古人Gönpo Tsering和甘丹江孜寺的Trehor Tau Tsewang Gönpo。第三名是哲蚌洛色林寺的Loseling Demo 杜固仁波切和我。
那些获得名次的按照名次排队,那些没有获得名次的则按照剃度的年头排队。那位Hotogtu因为没有获得名次,他的法座连同靠背等都安放在我们6人队伍的最后、靠近大门,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人人都收到茶叶和大米,获得最高名次的都得到表示祝贺的奖品。我和Demo仁波切因为获得了第三名,得到的奖品是法袍、zän袍,黄帽,丝绸哈达和两块茶砖。
这样,我在公开辩论和质询时勉强能够免于在那些博士面前丢脸。在我看来,如果不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通过细致的分析研究,使自己熟悉掌握那些经文的内涵、并将其刻印在自己头脑中,平时偷懒、仅仅依靠自己的智力去理解经文,那么一旦过了考试,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理解和记忆就会像彩虹一样消逝,最后留下的只有一场似曾相识的梦幻。
大法会的公开辩论结束后,像那些阿罗汉所说的那样,“我干完活了!除了此生,我再也不想再一次重生了!”我们连接好些天都放松自己,不再苦读。后来,在历次举行祈祷和大会的间隙,Sherab Gyatso格西再次去罗布林卡宫校对《甘珠尔》,我每天都跟他一起去,受获《Root Text On Poetry》和根据妙音天女的《Song Of Joy》著述所作的教诫。他教授“现量相”时,由于只用带比喻的音步诗句教授,而且我已经有些熟悉该主题,我能够立刻想出比喻诗句来应对。虽然我打算最终向他学习最先和最后的章节,却因为密院的学习日程有安排、而且还要参加其他的教诫而放到一边。
由于额外增加了“孕”月,土羊年2月荟供法会期间,我应召去罗布林卡Kälzang宫,当时13世嘉瓦仁波切、至圣荣华善妙世尊Jetsun Ngawang Lozang Thubtän Gyatso Jigdräl Wangchug担当主持和上师, Deyang Tsänzhab仁波切 Tänzin Trinlä Özer担当揭秘,Namdra Dükor Lobpön Jampa Sönam任计时,江孜寺 Chöje 哲蚌洛色林寺Trehor Jampa Chödrag和Sharpa Chöje色拉寺Je Lawa Lozang Gyältsän等都在场,我在由10位住持和上师组成的僧伽会众的中心受获Bikshu誓愿。
我想在此做写解释。从我到Gän 仁波切的僧寮时起,到我入密院止,我们凌晨即起为长寿而一同念诵宗喀巴上师瑜伽法、《念诵文殊诸名》(Expression of the Names of Manjusri)及大威德金刚仪轨。念诵完毕,直到早餐备好前,我都会至少背诵1页半当时正在修习的长页体版本经论。早茶后,按照密院四季的不同,我每天都会参加辩论庭的早课和傍晚的度母法会以及辩论,晚上一直讨论上师的教诫,通常都是到10点以后。
早晨的仪式和中午的辩论间隙,我要么得去受获Gän 仁波切的教诫,要么继续与佛法学伴Ngawang Lozang或者别人学习讨论。冬课期间天气十分寒冷,每年我的耳朵和双手都会冻伤,裂开口子并且流脓。但我从来不为其所扰,每场辩论课都到场。
在拉萨的学习间隙,早课结束后,Gän 仁波切 会在ling kor上绕佛。我小的时候,到了这当儿就是玩耍和画画等的机会。Gän 仁波切将要回来的时候,附近或者我前面的地方总有一声急促而大声的敲门声,这时我会迅速把玩具收起来,假装在学习经文,这样就可以在Gän 仁波切回来的时候避免遭到责备。因为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会一直玩到敲门声响起。
在我还是一个玩耍的孩童时,那位名叫嘉钦多杰雄登的护法像一位慈母一样无数次关心我。在拉萨的学习间隙,有一次天已经黑了,我得出去念诵经文直到10点或11点。当时,如果我没有记住经文或者漏了经文,睡着了,或者发音不清,回来时就会遭到Gän 仁波切一阵暴雨似的打骂。
直到学习《中观》的第一年,每年的冬课期间,学匠们都要在扎仓的珍宝住持面前背诵经文,如果谁能背到1000页,就能得到一等奖。我有两到三年得到过一等奖。
我在拉萨的僧寮里有一本Nartang版的《甘珠尔》。另外,水鼠年拉萨发生了一次与汉人军队的激战,Tängyä Ling扎仓被毁。于是,政府把许多圣经和一整套手抄本《甘珠尔》托付给甘丹寺。而那些经文多年都一直保存在我的僧寮里。因为这个缘故,我到13岁、刚刚受获《经藏》传承,便开始阅读。我从13卷律藏传本开始,阅读的时候如痴如醉,最后把整部《经藏》都读完了,还把《论藏》一大半(包括《Collection of Praises》等章节以及经和续的许多主题)也读完了。
因为担心遭到Gän仁波切斥责,我会把半本经卷藏在床头的佛坛中,等Gän仁波切出去、还有几乎每天晚上,我念诵完自己背下的经文并且Gän仁波切就寝后,我会在床上就着灯读40到50页经文。另外,在拉萨和Chuzang闭关时,我还读了杰宗喀巴及其弟子们的作品集以及许多喇嘛(比如诸位嘉瓦仁波切和班禅喇嘛)的作品集和生平,以及有关经和续的各种杂论。
我阅读的范围十分广,仿佛没有什么经卷我没有读过。直到木鼠年我去乡城 前都不断进行这种随意的阅读。我在前藏和回到中藏的时候都继续阅读许多无派宗喇嘛的早期和后期作品。正如《Hundred Verses Of Wisdom》所言:
知识留驻在经文之中,
密咒尚未修习,
健忘的人所进行的学习,
到需要的时候,大多都会忘掉!
同样,就像一个孩童观看寺庙的表演,我阅读和观想这些经文的经历,如今不过像是那个寓言所讲的兔子的角而已!
经历那些格西大会和法会之后,我进入了荣耀的上密院,后又到了中藏的上密院Chudar院春季班,受获珍妙住持色拉美寺 Gyälrong Lozang Tsöndrü所传的密集金刚4部合疏。春季班结束,我参加了甘丹寺的夏季班、拉萨大朵玛仪式和修习献供,以及色拉寺的法课。其间,那年7月,在Drag Yerpa密院传统的夏末课期间,我参加了新任格西必须参加的所有课程、辩论考试、7日曼陀罗维度修学,还在众位住持和喇嘛面前参加了3天的Tig Chen(又称Great Lines)考试。
参加Tig Chen,考试期间,像从前一样,分别由一位住持和喇嘛向格西们讲授密2维密集金刚和3维曼陀罗的象征意义、胜乐金刚、怖畏金刚;仪式助手们受获了彩色曼陀罗沙。按照传统说法,那些初学者被问到那些3维曼陀罗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因为我在诸位格西前面,所以不得不回答那些问题,但由于Ngaram Dampa的恩慈,我得以直接答出所有的问题。
我们在Yerpa接受密集金刚4合疏教诫、胜乐金刚根本经和《Illumination of the Hidden Meaning》著述。那时,我前任的侄子Rigzin、Latsab Geshe和上密院的两人——Tzongzur Legshä几年前派这一行4人去蒙古Torgod接受供奉;此刻回来了。可把他们剩下的东西平分4份后,除了偿还他们启程时所备物品的本金和利息,他们一行的所得,除了应付他们的生活开支以外, 几乎一无所有。Gän仁波切和我就是在此时将处理家舍事物的责任转交给了Rigzin。Yerpa的课程结束后,我们继续去拉萨参加秋课、去甘丹寺参加Tse Dharma和冬课。
我20岁那一年是铁猴年,大法会结束后,我去Kyormolung 听取密院课程。按照密院早期的传统,杜固首次进入密院大会众中间,3天时间都要像普通的新戒那样必须参加所有的众会和辩论。3天后,他们得向密院官员进行程序十分繁杂的供茶,叫ne ja。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在会众当中原来的位置,可以有事请假等等,这与密院前任官员们所必须达到的要求相似。虽然允许我这样做,但过了1年后才有要求请假脱课的必要,但是此时我同其他普通的僧人一样参加每一场众会和讲法。这让密院和行者们十分欢喜。我如何坚守课程纪律,甚至成了他们后来向入密院的杜固们经常提到的榜样。
那一年,我参加了甘丹寺的冬课,应Mili格西Gedun邀请在Dokang 康村向大约300名僧人阅读口传了3卷本缘悲经集和扎什伦布寺的密续仪式祈祷本。
我入上密院按照课程上课,然后又倾听Chuzang闭关处的授课等等时候都没有固定僧寮,因此应甘丹江孜寺和萨济寺学院许多Gän仁波切的学僧要求,每年夏季闭关和冬季佛法课期间及其他时候,我们都去甘丹寺进行相应的修习,春季和秋季我们都呆在我在拉萨的僧寮里。
铁鸟年我21岁,那年春天我在Chuzang闭关处受获帕绷喀金刚持惠施,他对我施行金刚瑜伽母的辛都拉曼陀罗4灌顶和生起次第与圆滿次第精深教诫、萨迦派13金经随许灌顶、《Tagpu十三净观》、文殊教轮、《Close Lhodrag Lineage》,以及《多聞天十五教义》(Fifteen Vaishravana Teachings)等。
从当年Shölda后7个月的第三个月直到8个月当中的第六个月,97位格西(如Dragyab Obom Togdän Jamyang Lodrö)与一大群随员们受获了一群最尊贵大喇嘛施予的65次殊胜密多罗曼陀罗大灌顶,那些曼陀罗是出自Mitrajogi精心布局的108尊曼陀罗。每天早上施予一次低级仪轨灌顶,所以每天灌顶2次。准备4级仪轨当中的每一级灌顶都完整地进行,绝对不会为了简便而有所删减;每一次都是按照圣神传承上师们的传统做法进行。
那一年,由于哲蚌洛色林寺为财务主管的任命问题而发生争执,在几个不明真相、未入籍的僧人撺掇下,很多僧人聚集在罗布林卡宫的窗户下面行礼拜,还从上面的阳台上大声喊叫。为了遵守传统纪律,嘉瓦仁波切面带怒容、生气地招来肇事头目时,有个名叫Nyagre Gyao(“胡子Nyagre”)的据说已经逃跑并躲在Tölung一带。有些官兵还在达隆(Taglung)一带的山洞里搜寻他。甚到授法一旦开始以后,有些参加的人只要留了胡子就十分害怕,担心士兵会怀疑他们、来抓他们。
当时上课间隙,帕绷喀金刚持会向我讲授Ngag Tu、心咒集、金刚瑜伽母随许灌顶和法王drugchuma安乐与威怒朵玛。从Tagdrag闭关处返回Chuzang闭关处后,应Lhalü Lhacham Yangtzom Tsering女士要求,1000多名僧俗人等在喇嘛和杜固带领下在Nyangdrän Chuzang闭关处的佛法庭中,受获了许多体现一切皈依的脱体Lozang Tubwang 金刚持(杰帕绷喀)珍妙佛法。从8月30日开始,我们连续24天都受获Jampäl Shäl Lung的菩提道次地教义、文殊教义、中传承,以及相应的南传教义和Nyurlam Martri、《捷径宣喩》(Swift Path Explicit Instructions)等。有幸参加的僧众受获了综合这三个著述所得觉悟道路的详尽体验教诫,以及参加仪式受获愿行菩薩誓愿。
金刚持喇嘛授法时曾说:
“于有分別智者,此实博大精深,
于智下者,则好懂易记。”
因此,由于他的阐释方法十分高超,人人都很容易懂而不管他们的智力高下。又因为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进行教授而不唱高调,大家都能听懂,这让我这妄自尊大、如脱缰野马般的大脑在群山之间纵横驰骋,迈入平坦的佛法大道。即使我不停地头顶他惠泽恩慈的债务直到获得觉悟,都绝对无法偿还那份恩情债务。
Dagyab Dong Gong 杜固当时做了一些粗略的笔记,直到为了接引Jor Cho功德田the Preliminary Practice Ritual,帕绷喀金刚持亲自作了校正。在关注各方的敦促下,我将其前后的菩提道次地教义笔记进行了编辑,添加我根据自己微不足道的判断选取的教义内容,终成今天印刷出版的《Namdröl Lagchang,掌中解脱》。
当时,Chagong Bemda 杜固和Laka杜固都正从乡城来,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但Bemda杜固及其一行事先派出了使者请求嘉瓦仁波切,想接替拉萨的赤江拉章成为合法的转世,就像“鸟归巢、剑回鞘”,他和随从们在Amdo呆了一个多月等待答复。
Laka 杜固在Bemda杜固前面离开,来到我在Chuzang闭关处的僧寮。他说在甘丹寺的时候一定要我当他的老师,我同意了。
菩提道次地教义讲完我去了拉萨,到达Lingkor东北部的Mindröl桥时,正赶上Bemda杜固一行首次到达拉萨、受到色拉寺Mey Pomra Geshe Dapön的迎接。这种巧事发生的概率简直像碰见寓言中的海龟脖子藏在金壳里浮在海面一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Bemda杜固的请求得到的答复是:“根据种种迹象和事实认定的真正赤江杜固在甘丹佛教大学学习,甚至受获了格西拉让巴学位。他目前在荣华上密院修读课程。让你接替赤江拉章根本不合适!去你父辈家谱决定的佛寺吧!”答复如此,这位杜固便进了色拉美寺扎仓。这位杜固的亲戚,一位谦卑的“益喜格西”在他去世之后回到他的家乡,给我看了向嘉瓦仁波切之前的那位Ta Lama递交的类似请求副本,并请求我原谅其在过去带来这么多麻烦。
菩提道次地教义传授结束,我休息了几天,接着,帕绷喀金刚持携带随员60人在Chuzang闭关传授一种修习教义(此修习由百千万悉陀流传,受到诸金刚瑜伽母珍崇)、至高无上最秘密续集、荣华甘达巴派胜乐金刚外五尊灌顶和胜乐金刚体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曼陀罗修行,以及《那若巴六瑜伽》教诫,我也非常幸运地受获这些教诫。晚上,讲经结束后,我们几个上了一堂复习课,并受获了需要与六瑜伽同时修习的体操等内容的详细教诫。有天晚上,我们正在跟着那位珍宝喇嘛修习灌瓶屏息和练习体操。周围万籁俱静,突然,后面有个人放了个很响亮的屁!喇嘛和大家哄然大笑,只好休息一会。
我22岁时是水狗年,大法会过后,遵照嘉瓦仁波切的指示,帕绷喀金刚持在拉萨须弥云堂、在大约4000名僧众面前传授中等长度的菩提道次地著述。我们都去参加。荟供法会结束后,Kyabdag塔普金刚持Lozang Jampäl Tänpay Ngödrub(又称Padmavajra尊者)从Barkam来到拉萨。他在Kashag Lho的时候,我有幸在他脚下膜拜。
应大臣Shölkangpa之子Sharpa杜固要求,他给我和7位至高圣者(包括Tagdrag 金刚持、甘丹 Tridag 仁波切和哲蚌寺Mogchog仁波切)惠施了30多次灌顶,并用他的净观教诫了各种精深的修习法。我们大脑的容器盛满了无上福德。有一天,我应邀去这位Vajrahara上师的僧寮,受获他惠赐直达麻利度母“入心”随许灌顶Tangtong密传长生灌顶、晋美(Chime Pälter)荣华长生珍宝。
Tagpu Tänpay Gyältsän、Garwang仁波切和其他的人认为,塔普金刚持经常看见诸位上师和诸明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经常面见度母,就像两位常人会面一样,受获不可思议密教和懸記,装满了1个“母卷”和大约3个“子卷”。因他是个大士,代表着无限的曼陀罗,我请求他懸記我的禅天和我后世所去何地。他询问度母,她示现了8行诗。如果那不是欺骗,就是一种让人喜乐安睡的诗。
Kagyur Lama 仁波切 Lozang Döndän Pälzangpo对我总是很仁慈。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僧寮说,“你没有受获宗喀巴大师和他两个弟子的作品集,听着,我给你讲!”。他既不要供奉,我也不需要向他请求教诫。但就像他所说的,他在密院中他不大的僧寮内乐意慈祥地向我阅传惠赐文殊父宗喀巴和其二子的经文集。当时我十分贫困,只能向他供养5 do-tsä的银子。
这事快要结束时,我又开始受获Kagyur喇嘛仁波切在Shide Nyangnä Lhakang惠传的5卷Tagpu Garwang经文集。当时,帕绷喀金刚持和若干喇嘛,杜固和格西(包括甘丹江孜寺 Tridag 仁波切、Gomang Mogchog仁波切、Tsona Göntse 仁波切和我们自己)在拉萨Shäzur僧寮心专心致志地精研修习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的3维曼陀罗。
我23岁那年是水猪年。我在Chuzang闭关处受获帕绷喀金刚持根据zamatog “觉器”13尊畏金刚所慧施的Bari Gyatsa随许灌顶(Bari传承的百明王灌顶)、仪轨大海Drubtab Gyatso随许灌顶、Nartang Gyatsa(Nartang传承的百明王灌顶),还有根据其亲身体验讲解的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著述;和对《瑜伽上师》、《Chöpa喇嘛大道大手印》、上师荟供,以及大手印根本经文的著述,还有其他各种经传和著述,如有关如何进行怖畏金刚Pawo Chigpa唯雄大闭关的著述。
正如前文所说,管理我们家舍的责任此时已经交给了Tzöpa Rigtzin。我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他对于管理事物既知之甚少,又无计可施,并且他好玩掷骰子游戏,因而无暇管理。这样一来,就像肉给出去却一滴也收不回来的故事那样,我和Gän仁波切的吃喝有时候不能按时送到。
当时的代理大臣是Kalön Kemä Zhabpä Rinchen Wang-gyäl,因为他是一位最强势的人,因此如果受到他的帮助保护,就很可能出现只要他说什么就必须照办的情形,于是我们带了一点供奉给Kunzang Tserkong,向他详细讲了我们的情形。我们要求发布命令以进行应有的调查,因为Rigzin的想法和行为都反复无常。他回答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杜固除了有时候给一点建议之外,还要承担管理责任。就像常说的那样,‘我是自己的保护人。别人谁会保护我呢?’如果你们不能供养自己,想要别人供养自己真是不当!而且,就像Je Ba Rawa Gyältsän Pälzang所说的那样,
‘虽然亲戚朋友都是平等关系,
有钱的时候他们对你殷勤周到,
如果你一无所有,厄运临头,
他们会不理不睬,你不值一提,地位下降,
艰难时期的牢固朋友十分稀奇’”。
想起此事令人忍不住要哽咽,也清楚了从亲友身上能得到什么指望。
我开始在上密院上课以后,固定的僧寮主要在Chuzang 闭关处,但无论帕绷喀金刚持在哪里讲经我都会过去。这一年的早些和晚些时候,在课程间隙我会练习金刚瑜伽母、怖畏金剛唯雄和十三尊、Gandipa五尊胜乐金刚、马头明王密传、Pälmo法大悲者等等lä-rung闭关,希望主要通过在菩提道次地禅定上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而取得心界进步,并且结合初步修习淨心和累积功德来进行。
但是,不久以后,其他因缘让我必须去乡城或者其他地方照顾一些令人分心的事务,因此在观想和禅定方面即使有所体验,这方面的迹象也像冬天的雾气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我想,这是因为以前诸世犯下许多违背功德的行径造成的结果。
我24岁的时候是木鼠年,僧众决定我应当去乡城寺,因为该寺所在地区的民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不断督促。大法会结束后,我请求允许我免于修习密院课程。我打点起自己的禅定坐垫,正赶上当天林金刚持Chogtrül 仁波切刚进院铺开自己的坐垫;当时我正与会众一起举行最后一次用茶仪式。
荟供法会完毕,应甘丹萨济寺 Dokang Samling Geshe Yöntän要求,我给大约200名在座的僧伽念传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弟子们的作品集。当时我每天念一卷。我的舌头不能像别人的那样一天念两到三卷。
当时,色拉美寺Pomra 乡城 Pälchug Dapön Geshe和Kroti Tsultrim等人再次对我们到前藏提出异议,向嘉瓦仁波切的辅臣Tsarongpa Dazang Dradül递交了请愿书。有一天,应一位名叫Zhide Ta喇嘛的政府代表要求,我们把一位淸淨僧人请到我的僧寮。他对喇嘛金刚持的教诫非常恭敬,言听计从,此前几次曾替他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担任嘉钦多杰雄登的神谕。我们请求他提建议。这是因为我们对前藏有什么问题没有把握,也想知道我在前藏的时候假如让康村管理僧寮好不好。我们得到的传话是这样的:
珍宝伞是防晒的无上器具。
(这指的是嘉瓦仁波切。)
金鱼为心的嘱累,大海洋中的功德,(指的是Khamtsän寺。)
所欲瓶中装有许多敌人之诸法,(许多妄修者的本性,)
莲花(太阳)之友不需阻拦月亮(不外观以自为)
如法螺的声音不说别的,
只有出自无尽密心结的甘丹口头传承,
我要做威怒轮宣告胜利
高举佛法胜利之旗帜!
这些就是我们受获的预言。
大约在此事结束的时候,应Trehor Kartze Trungsar 仁波切要求,Kyabdag Kagyurwa Chenpo Jetsun Lozang Döndän Pälzangpo尊者向中藏大约80位喇嘛和杜固念传了Tukwan Chökyi Nyima的作品集,其中包括原先密封的经文,还应Pangda的Chötsün Trinlä Dechen要求,向大约60名僧俗人等,惠施金刚瑜伽母加持和生起次第及圆满次第教诫,还向约200名随员惠施五尊甘达巴胜乐金刚灌顶和马头明王秘密大灌顶。
回前藏的时间临近了,我获得召见,向嘉瓦仁波切无上尊者的莲花足礼拜,受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在前藏做事的教诫。
遵照嘉瓦仁波切无上尊者的吩咐,我去Yarlam向众人礼拜道别,当时那里正是夏季闭关期间,Kagyurwa尊豪Jetsün Lozang Döndän Chogtse正在讲授《别解脱戒》(Pratimoksha Sutra)。所有师傅都聚集在哲蚌洛色林寺扎仓,帕绷喀金刚持正在教诫《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是我去了他在Kungarawa宫的僧寮,向其礼拜并道别。他无上仁慈地惠施我精妙广泛的告诫,恍如蜜露滋润我心田,内容包括需要在前藏广布清静甘丹传承等,还惠赐我许多礼品。
正像我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由于我的家舍中Rigzin行为不检,我们担心自己在前藏期间管理会出问题,于是请甘丹寺 Dokang 康村担起责任。我请康村照管我的僧寮和位于Meldro的几块甘丹大会众土地田头交上来的租金。照管在拉萨的僧寮责任、收取的萨济寺和Dechen Lamotse以及Gyamag的地租应当在管家Rigzin手里,但虽然收到300 tamdo租金,我们回前藏后要将其中的200 tamdo还给康村,100要还给他本人,包括要支付给康村的 200 tamdo,所以我们给康村积攒了更多的债务,除了先前的债务外,我们仍然要向Rigzin借取和偿还小额债务!
同时,由于新旧执事交替、我本人格西典礼费用要偿还等等,加上沉重的义务,实际收取的租金难以抵消,所以我们准备返回前藏途中所用的全部物品困难相当大。不过,通过请求我的一些弟子和施主拔助与借贷,我们勉强凑足了所需。7月,我、我的随侍Lhabu、仪典侍者、来自Markam的上密院 Ngagram Zedru Göndra Budor、我的法友Gyütö Pukang Lozang Tashi、厨子Namgyäl Dorje、裁缝Tenzin Lhawang、两个照看马、驴等的马夫(其中一个是Sönam Wangdü)启程了。4个打前站的护卫(其中一人是Tändrong Pälbar Togme)从拉萨动身,在Yarlam 贡塘呆了两天。
我向自己的出胎护法Dragshul Wangpo、还有Nyima Zhönnu本人还有随从等人发出请求后,护送我的不是Tzöpa Rigzin,而是一位来到前藏的本尊Tsängö(他是Dragshul Wangpo的使者)给我提出种种建议,让我留意自己的健康、饮食、行装、沿途所遇到的大岔路口等;这事说起来还真是有趣!
接着我们出发了,我和母亲和妹妹Dechen Karab Ogong在Dechen Karab Ogong家呆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到了甘丹寺,与Gän 仁波切 Lozang Tsultrim进行了一次轻松的见面。我逗留期间,用两天时间给Dokang康村云堂的500多名僧人做了十三尊大威德金刚大灌顶,用1天时间给宗喀巴大师舍利塔Serdong Chenmo供奉并在灌顶山上做了sang(香烟供)。
接着,我应邀去了萨济寺的学院。住持的使者Pukang Lozang Kyenrab举起该院送的觉悟身语义像供时,为每尊像念诵了一首经文。他在念诵舍利塔的经文时,这样说道:
käl pa je wa sam yä su
chöd-tän tzä ching zhug gyur chig
请于不可言说百十万劫,
矗立不动,为舍利塔!
因此,虽然他是非常著名的辩论和经文师,但在这里却显示了对于语法的知识是有欠缺的。
此时,乡城的人没有停止游击战。虽然他们发出非常响亮的喊声,但有些不信仰我的人也在场,使我很难从乡城返回西藏中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监视、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我从甘丹寺离开后,Gän仁波切一直呆在自己房间里。许多人虚伪地向Rigzin和康村的成员供奉,仿佛在算计他们还能在那里呆多久。帕绷喀金刚持于是说:
本应提供保护的雨云,
却泼下雨雪冰雹,击下一道道闪电。
即使是生命如此需要的阳光,
也像地狱之火一样熊熊燃烧!
情况好像就是这样。我支付了请求在甘丹寺安排长期住所的费用、主持了与朋友和法友的会见礼仪、在Serdong Chenmo 前做了供奉……如此等,手头只剩下大约15块银(silver sang),我把它奉献给了Gän仁波切。
我离开甘丹寺那天,Gän 仁波切泪流满面,显得对我慈爱有加。还给我提了许多珍贵恳切的建议,都是从是否离开甘丹寺的角度说的,我的内心对他充满了依恋之情,觉得离开他真是让我无法忍受。
我们在Mäldro Jara Do 的家里呆了两天,先后经过Richen Ling、Özer Gyang、Tsomo Rag;Kongpo、 Bala pass,以及Gyamda、Tro山路、Lharigo、Bändhala、Nubgong山路,沿途险象环生,有许多狭窄幽深的峡谷、高峻陡峭的悬崖和十分难行的桥,最后仿佛突然到达Ngödro。我们在那里、在仁慈的Ngaram Dampa 本寺Ari Monastery 呆了1天,做了简短的供奉。第二天,我们走进Dampa的寝室Ayig Tangowa 呆了一会,我给装了他舍利的泥像象征性地做了供奉。
我应拉章的邀请去了Gyatso Ling寺院,并在那呆了1天。前任Gungtrul仁波切曾向我传授许多密宗佛法传承,我在他舍利塔前做了许多供奉。那位现世Gyatso Ling杜固就住在那里,他好像很喜欢玩游戏,因为他还小。
我们穿过Shargong关口,到达Chagra Pälbar。我在那里应下密院 Ngarampa Pälbar Geshe Ngawang Chöjorchän要求,给大约10名Pälbar扎仓的僧伽讲授了新戒和具足戒。
我们先后经过Lhatse后Shopado,到达Tzitor,那里有Nyinpa和Sipa两座扎仓。应Nyinpa扎仓邀请,我们在那里住了3天。我给一座新建的弥勒像做了广大的怖畏金刚开光仪式Geleg Charbeb,是与这座扎仓的仪式僧一起做的,还为当地人做了长生灌顶。在众会的间隙,我还应Sibpa 扎仓和Drag Nag 拉章的邀请去做客,并举行了灌顶仪式等等。
然后,我们住在Lhotzong前任甘丹赤巴的最大施主家。应当地的Tram寺邀请,我去了一会,给那里的圣物做了开光仪式,并与当地的僧伽简短地结了法缘。
接着,我们经过Yidag pass,穿过Gyälmo Ngülchu河上的大桥,到达Wako的Mari Mountain。西藏政府管辖北部游牧民族大臣”Horchi” 派一名使者从Kyungpo Tengchen捎来口信,让我们在Mari Mountain等他,于是我们就在Mari Mountain等了1天。第二天,大臣与他的使者们到了,我与他进行了1天轻松的会见,给他做了Drubgyäl派长生灌顶。 我还向他进献了Känchung慷慨给予的金钱,还有沿途收到的少量供奉,并吩咐做两个镀金枕头饰物供奉给Dokang 康村。
那位刚才提到的Känchung不是别人,就是在Sangpu庙翻修时,遵照嘉瓦仁波切命令,担任政府指派首席监督的人。我当时正在夏季闭关,很喜欢学习的内容,包括去寺里的庭院对引用的经文和逻辑进行辩论。按照吩咐,我要写一篇内容广泛的翻修回向文,要写在庙墙上。我在诗中嵌入了第13世嘉瓦仁波切Ngagwang Lozang Thubtän Gyatso Jigdräl Wangchug Choglä Namgyälway De的名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这位法友,他忠诚佛法的话语解脱了信徒,引出法力无边、让人心醉神迷的莲花芳香,
他已穿越佛法的大海,佛法是大能者指引众生度过轮回与涅磐的明灯、伟大教诲。
毫无畏惧、无与伦比、光照一切之主,战神一切魔恶,
众生的太阳,十大威力的化身,我向您膜拜,用我的头顶!……
我用这样的话语开头,表达了对于皈依主的敬意,有些诗句表达了作意和誓愿。从此以后,那些诗句成为每当供奉经常会念诵的句子。
接着,我们先后经过Tsawa、Pomda、Tzogang等地,到达芒康,在靠近一个叫Kongjo关的地方住了1晚。夜里我梦见一个人,像是我妹妹Kuntse Cham Dekyi Yangchän,只见她穿着花哨的衣服,带着花哨的珠宝,露出各种开心的表情。她把我带进一座像红色的布达拉宫的很大的城堡。一座庙里有许多房间,庙里有觉悟身语义像,还有许多供品和僧人。
她还带我慢慢地走上室内的一道楼梯,楼梯是镀金的。她还给了我一些吃的喝的。第二天,在与当地人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当地有一个叫Pawo Trobar的神主,他有一个妹妹叫Tachang Ma,我想那一定是他们的某种化身。(后来,在1964年,我在达兰萨拉通过康巴族女人Namgyäl Drölma通灵,才与Trobar 和Tachang Ma 直接接触,Tachang Ma 告诉我说,我从前经过他们所在地方时,她通过托梦直接给了我一些示意,这印证了我以前的想法。)第二天,我们穿过一条名叫Dachu河上的大桥。所有人、马和驴子都用绳索收紧,绳索一头拴着系在一起的牦牛。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很害怕,但最后还是安然无恙地过了河,到达芒康的Gartog。我住在芒康Özer寺的拉章 中的住所。Özer仁波切的前世住在拉萨的时候,我们来往非常频繁。因此我到前藏的时候,他非常慷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离开了Gartog,在Marlam Lhadün,看见了一座庙还有里面十分有名的大日如来佛石头雕像(称为Chagzo);那位中国皇后Gyaza去见皇帝时曾从庙旁经过。我们到达芒康Zeudru寺那天,大成就者之主、Gangkar喇嘛仁波切Könchog Chödrag来到寺前的前哨城堡接应,我在寺里新建的拉章寓所住了几天。
Gangkar仁波切以前是在哲蚌洛色林寺居住的。虽然他对经文不是非常精通(因为他呆在那里学习的时间不长),可他通过体验达到很高层次的证悟,因此有许多直视无碍的天眼通,而且是一名大瑜伽掘藏师,曾从一些湖里和石山上找到许多雕像、三昧耶实物和珍宝。他始终是个清净受戒僧,修练甘丹传承的净观和修习法。
虽然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但由于我们彼此的杜固之间有许多世的业缘,因此我住在西藏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给寺里的僧伽做了13尊怖畏金刚灌顶,给僧俗大众做了大慈悲者观世音大灌顶。喇嘛仁波切送给我一尊天然形成的青铜胜乐金刚像,是他从Bumtso湖中间的岩石中得来的,我现在仍随时带在身边。
接着,我们在Gowo Rong Gönsar寺的上寺附近穿过Drichu河,走了一条狭窄陡峭的路,叫tramko lam,最后到达Tzetze寺,那里住着一位叫Dranag Lama(又叫Chöpag喇嘛)的上师,我在西藏接受經藏《甘珠尔》传承的时候,他是我的学友。离别后,他曾修习施身法(chöd),曾看见许多神灵和天道众生的身影。
从贡布到康区的许多寺庙,如果他在会众聚会的间隙修习施身法和其他内容,那些参加的人就会在晚上,听到屋子里里外外各个地方传来有人用汉语、藏语和许多不同的语言发出的支离破碎的声音,还有枪炮会莫名其妙地走火,还有数许多钱的声音、痛苦叫喊的声音等,还有出现人人都能听见看到的各种身影和声音。因此,人们渐渐认为他是Lobpön 仁波切,莲花生大士的化身,于是人人都对他十分信仰和恭敬。
他的佛法业行一天天增长。最后,依照公众的意愿,由于汉藏之间爆发了冲突,他担任了类似大将军的职位,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士兵们手拿武器,身披铠甲,驻扎在Tzetze寺内外。因为我曾是他的学友,按照当地的风俗,应他的要求并遵循嘉瓦仁波切和其他人的指示,虽然有一些坏人冒充喇嘛,他却特别重视我的意见和建议。我与那里的僧伽结下了佛法因缘。
接着,我在嘉瓦仁波切Gyälwa Tsultrim Gyatso到达的Shogdrug Drodog村住了一天。我们在那里碰见从乡城寺地区赶来的一支50名骑士组成的护卫队。我经过Ragtag寺等地方,到达乡城家,在那里住了1天。这时有一些官员到来了,比如Samling寺住持的使者Nyanang Drodru Geshe Lozang Tarchin等。
我以前在该寺的时候,Drodru格西是该寺的领诵师,每当Gän仁波切责骂或打我的时候,他就会替我求情等。我俩彼此有深厚的感情,那天重逢的时候十分开心。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我们到达乡城桑培林寺。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可虽然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歇息,内心却期待见到各色人等。
木牛年我27岁。那年1月,该寺举行新年法会,我每天早上都去辩经的庭院。到了教授传统的三十四本生经的时间,因为经文是用诗文写成的,许多僧俗人等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经文了,那是一种变通的办法,为的是方便人们理解和证悟。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打架偷窃,面对因果报应的自然法则不晓得选哪一个,于是我便用乡城当地通俗易懂的口语讲解了《贤愚经》。
法会结束后,应该寺众人和当地普通民众的要求,我在该寺的石头庭院里给大约5千名僧伽和居士做了华摩派大慈悲者千手观音大灌顶。灌顶当天,我进行瓶灌时,天上下起了小雨,天边出现了彩虹,诸天和龙神等吉兆也示现了。
由于Luchun的军队结下的恶缘,该寺许多年都人去楼空,就连当地人都逃散到山里。为了众生、地球、环境、诸天和龙神还有当地的神主的福祉,以拯救恶化的世道,我用净瓶撒了净水,念诵了1200遍缘悲经,成熟和圆满了那些地方,并传布给该地区整个上下各处的本地人,还做了藏护(protective concealment)仪式。
那年3月,我在该寺云堂,给大约2千名听众——该寺的僧伽和当地民众,讲解了15天的菩提道次第(Nyur Lam),最后做了菩提供养。接着,我给大约500名发愿每天念诵六支上师瑜伽和100遍缘悲经的居士和僧伽做了13尊怖畏金刚大灌顶,用了两天,包括一天预备时间;然后我给148名发愿每天修习勇猛怖畏金刚成就法的善士,做了勇猛怖畏金刚大灌顶。对63名发愿长期进行怖畏金刚闭关的善士,我详细讲解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瑜伽,还有如何做长期闭关,这全都是按照金刚持喇嘛定下的传统程序做的。
4月,因为打算给该寺修建一座新的主圣物——一尊镀金米勒菩萨像,我便派我的侍从Lhabu还有其他几个人去拉萨采购所需的物料、珍宝装饰品等等,我还派他们请求第13世嘉瓦仁波切、帕绷喀金刚持、Kagyur Lama 仁波切、Gän Yongzin 仁波切 Lozang Tsültrim、Geshe Sherab仁波切等加以护佑。那些喇嘛都是我的皈依主,因为我曾与他们结过法缘;我还让他们向帕绷喀金刚持和托摩格西仁波切昂旺格桑分别捎了一封诗体请求信,给东嘎寺嘉钦雄登神谕捎一封信,请求他详细预言乡城的情况。
我到乡城的前一年,有一位非常著名、叫乡城 Butsa Bugän 的人,被Chagzha Tänpa和乡城地区的其他人秘密杀死,那些人如果厌恶或嫉妒谁,就用神秘的方法让他们得心脏病;另外,当时乡城府库里有许多钱丢失,因此大家都知道当地偷窃横行。乡城寺和乡城地区的主要在家和出家官员(其中有些人站在Bugän一边)利用Bugän得心脏病这件事做借口,谋取私利,“翻山倒海”通过其在上下乡城, Gang Kar Ling、 Dabpa、 Mebo及Mongra等地的关系,召集一切可能成为军人的人,还号召Bai Sasung Gopön和中国Marsiling军队帮助他们。 人们认出乡城 Chagzha Tänpa 和他的“那帮贼”、就要抓住他们的时候,乡城 Chagzha Tänpa带着许多人跑到前面提到的Chöpag 喇嘛所住的Tzetze 寺,请求他领导他们。
从乡城寺和乡城地区出发的军队正打算离开,我尽我所能地向他们说明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可难以预料的是根据人的欲望采取的行动能不能把他们带到他们想到的地方,同样,我衷心的劝告没有让他们改弦更张,他们置若罔闻,于是大军离开了。 不仅如此,而且有人还在寺里偷偷地突然放火,把几个忠于Chagzha Tänpa的僧人烧死在他们自己的僧寮里;有些则被杀死在自己家,如此等,做了许多可怕的事。就像Zhangzhung Chöwang Dragpa所说的那样:
心肠已硬的人,你可以带他
登上洁净无瑕的水晶阶梯,
但就连天帝释也无法使他
登上妙善的胜乐殿堂。
那些事发生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未法时代像我这样的上师,只能遇到这样的弟子!。”可也无法可想。
当时Dranag喇嘛已经在Tzetze寺召集了一支强大的部队,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所以,乡城的队伍只能把他们围起来,却不能攻入寺中。僵局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
寺里举行夏季闭关期间,我进行密集金刚阿閦佛lärung 闭关。然后,因为开战等等原因,没有一点清净;又因为Gönkar Ling 和当地人曾邀请过我,我便带了几个特别能干的随从,经过“Mongra”“地区,到了Gangling Tso Togpön 的住所。
我在那里大约住了15天,期间应一些发愿者的请求,做了5尊刚塔帕胜乐金刚灌顶和金刚瑜伽母辛都拉灌顶,还简介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习法。后来,与我曾是同班同学的Gangling Sherab杜固,与Gangling寺的僧伽一同到来,于是我们在这许多人的护卫下到达Gangling寺。
我给那里的大约400人包括僧伽,做了两天密集金刚阿閦佛灌顶,依照的是一幅曼陀罗画,其中一天做准备。我还给1千多人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和长生灌顶。
接着,我们和Sherab杜固应甘丹寺赤巴前任檀越Nyingkung Bumtze Bälsä Pön的邀请,走了两天,到了Pön家宅,住了大约10天。我还给我们的随从还有当地居民和工人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和长生灌顶。我还给他们的甘珠尔庙(Kangyur temple)和护法庙进行了念诵加持、在他们的府库做了多闻天王兴旺仪式。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打算去Yarlam Gangkar一个叫Rigsum Gönpo(三派之主) 的地方朝圣,却在Tsogo闭关处住了下来,大概做了3周类似于刚塔帕派5尊胜乐金刚闭关,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念诵心咒。当时的情形是非常祥和愉快,因为听不到痴迷辩论的声音,还因为Zeudru寺的前任灵童、权势很大的Gangkar 喇嘛仁波切(称为“Gunkar”喇嘛)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进行禅修。
我给Gangkar的一些僧伽和几个朝圣者做了三派主长生灌顶。我们呆在Tzetze 寺的那些天,Dranag Lama Chöpag 的大仆人和他的一个乡城的仇敌邪恶地密谋,贿赂了喇嘛队伍中的一个人。那人在深夜走到喇嘛的僧房,假装让喇嘛为喇嘛妹妹的病占卜。
他喊了一声,大仆人便打开门,那人一进去,就向躺在床上的Chöpag喇嘛砍去。之前人们经常谈论说喇嘛有天眼通和神异力量,可在他需要的关头,却没能发挥出来。 这就像从前Maudgyalyana被云游的行者打了的情形一样。忘了那些所谓的神异力量吧,据说Maudgyalyana甚至都想不起来有神异力量这回事,这次的情况完全一样。
这样一来,喇嘛麾下的部队变成了一只无头的死尸,而敌军也在战场呆得太久,许多人早已一个个悄悄回家了。双方都结束了战斗。各自表达了后悔之意,战斗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一切又归于平静。我离开了自己呆的地方,路上在Gangling Zipön的住处停了下来,给当时在那里的人们做了长生灌顶,口传摩尼心咒,等等。接着又在Gankar Ling 寺住了几天。藏历12月,我经由Me O 回到乡城寺。
我26岁时是火虎年,这年的大法会期间,我利用在该寺授课的间隙重新讲解取自组织者Loba Goba经历的《贤愚经》等等。我听见有人说:“他讲解完了佛法,不知道说什么,就讲故事!”
该寺春节授课期间我按照鲁依巴派胜乐金刚所要达到的lärung要求进行闭关,还在这段时间的前后进行Kunrig闭关。夏季闭关期间,我按照鲁依巴大上师的学派传承对僧伽做了六十二尊胜乐金刚灌顶、Kunrig大灌顶和Rinjung Gyatsa随许灌顶。
那年4月,我的随侍Lhabu与同伴们一道从拉萨返回,带来了第13世嘉瓦仁波切的信、帕绷喀金刚持和Sherab格西仁波切的信(后面两位上师的信都配有诗句),还有Gän仁波切和其他朋友的信。 他们为弥勒佛的新雕像奉送了珠宝庄严和许多经卷还有加持的物件放在像中。
前一年在昌都 ,Lhabu动身去拉萨还没走多远,应Lhabu的请求,Domä Chikyab Kalön Trimönpa Norbu Wangyäl便已派两人寻找昌都-Tzachu河地区最好的佛像雕刻工匠。工匠找到了,他们与Lhabu 他们一起赶到,开始雕刻佛像。
在乡城地区最好的工匠帮助下,他们连续干了3个月,完成了一座3层楼高的弥勒佛镀金佛像。 佛像里面有4类心咒舍利、5类大心咒舍利等,都是法身舍利,还有如来佛頂骨舍利、一尊原为甘丹寺下院圣物、带有佛祖手印的Jamgön 宗喀巴雕像;印度与西藏许多大士的舍利(许多是他们的头发、法轮以及男女夜叉财神的宝瓶等)。
所有这些圣物加持念咒后,都要放到弥勒佛佛像里头,我在一群细心而合格的行者协助下,亲手把每一样东西放进去;要求佛像放在寺里的大云堂中。工程自始至终都详尽记录了各项开支,放入佛像的圣物和加持物也都做了记录。弥勒佛庙墙上还列举了制作佛像、行大礼已经供奉的各种功德等等。
所有主要供奉完成后,进行水鉢千供、点灯供奉、点长明灯等的时候,由我自己亲自担任金刚师,与20名修习过怖畏金刚的比丘,自始至终都用繁复的Geleg Charbeb 仪式对雕像进行开光。提到具体的施主姓名时,该寺的上师和我还有那些僧伽就念诵复杂的祈祷文,比如赞颂吉祥八宝等。
完成所有一切后,应Yangteng扎仓的邀请,我去了Yangteng寺给发誓愿者做了10天菩提道次第Nyurlam、13尊怖畏金刚大灌顶,和许多其他的灌顶和随许灌顶。然后,我继续在周围的Säl Lha, Dechen, Tsang 等地方来回,根据当地人的兴趣教授佛法,然后又回到乡城寺。
乡城寺早先的供奉传统是通过修习和自入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壇城、大黑天和法王(像在Gyütö扎仓一样用仪式旋律和音乐)、吉祥天女、多闻天王大法会、金甲衣念诵和旋律,还有按照甘丹寺萨济寺的传统行马头金刚大法会。
同时,因为该寺被毁,只剩下几个上师,有许多年人们都忘记了念诵的旋律,因此修持没落很多。因此,我从Markam地区的Lura寺邀请了名叫Bu Sönam的上密院密续专家。他和该寺住持的代表、甘丹寺萨济寺Drodru前任领诵Lozang Tharchin格西——他俩受过专门培训,熟悉该寺50名修习过上述念诵法,还有其他修习内容的大僧。接着,Bu Sönam,制作弥勒佛雕像的工匠们包括昌都的两名雕刻匠,都受获了供奉和祝贺,然后各自回了家。
因为寺里没有除障跳神法会(Gutor Cham)全套的服装,我们前一年用最好的布料修补增添了服装。11月,为了重开法会,我们请来了几个僧人扮演丑角,依照芒康的Özer寺的传统做法表演六臂玛哈噶拉跳神舞会。
12月,应Nangzang寺的反复邀请,我经由Pälshar寺和Gobo Pälbar寺前往,最后到了Nangzang Pälgyäling。 我在那里给大约700名僧人做了密集金刚东方不动如来大灌顶,并给所有人做了东方不动如来大灌顶。我还为Gän Yongzin仁波切 Lozang Tsultrim 度生日供奉了一些金钱和衣物。
我27岁那一年是火兔年,举行祈祷节的时候我回到乡城寺,在法会期间讲经的时候,我还从头到尾讲解了噶登派经文的子经Kadam Buchö。满临祈愿大法会结束后,我应该寺住持Drodru Geshe的要求,给大约80名发愿每天念诵上师荟供的僧伽讲解了上师荟供,共讲了25天。
这时,Gangkar Lama Könchog Chödrag仁波切带来了一封,信中这样说:
“在您的前生,有一个魔鬼对头,他心存恶念。他有许多巢穴,乡城有一座山,山顶上也有他的一个洞穴,形状就像一条尾下头上的鱼。洞穴底部有一条溪流流向山脚下的大河。靠近溪流流进大河的地方住着几个麻风病人,洞里住着一龙族,向人们下咒。如果我过去,可以做个法事把它赶走,但很困难,因此必须做一个适格的护轮(经咒),做个法事把经咒藏在洞里。那个洞从你在乡城寺僧寮的中部顶上可以看得见…。”
他在信里强调做个符很重要,因此我同住持Drodru格西还有10名修过大威德金刚的僧侣一道做了个适格的护轮。大家派Drodru格西和他的随侍Ngaram Budor前往,他们果然找到了那座山、洞穴和河,和Ngaram Budor Gankar讲的一模一样。他俩在那里作法埋了护轮。那一年11月,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突然从寺的南方传来一声好像迫击炮发射的巨响。后来又响了一声。起初大家摸不清头脑,后来干脆把它当成打雷,虽然乡城一带不大听到雷声,但大家没有怀疑会是什么。后来,住在附近的人说有闪电击中了山顶埋护轮的地方。
后来,我到了拉萨,有一位名叫Tsewang Gyältsän的宁玛派法僧对我说:“在您的前生有一个sorceror,他在康区和中藏欺压别人。您在康区打下那两道雷电,把他消灭了。现在,噶当寺前面有一条喷泉。您必须在那里立一个护轮!”
只有我和Lhabu知道乡城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人们说Tsewang Gyältsän有天眼通的说法看来是真的,而且那个护轮做得达到了要求。
资深的僧侣Pälbar Chödrag和Pälchug Dampa Chödrag也对我说了一些事,大意是“您从康区到与您有佛缘的西藏各地去,比如去拜谒那三所佛教大学、两所密院、各种kamtsän和家族,以及拉萨传昭大法会等,都要进行大量的布施和供奉,这必然开支巨大。您沿途偶然获得的少量供奉不够,因此我们做点生意,我们俩一起,通过昌都用驴子和马做。我们肯定会做,用所得的收益协助您。您的手下就不用干活。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本钱和利息,还有拳头砸在桌上的声音,和丰厚的供奉仪式。 ”正如《Eloquence of the Sakyas》所说的那样:
骗子的甜言蜜语,
是为了自私目的,
猛禽的鸣叫,
是个凶兆,不是快乐!
由于不知道这是个诡计,就像被一个愣头小伙所骗,并且这两个人是最好的寺院会众当中最稳定可靠的人,估计是无私而且我们与之有缘的人。于是我答应了。 他们实际启动的资金是3万中国货币元(tram chen),还有20只小骡子和几只大骡子。他们没有把话说明,但摆出手头有很多的样子。
后来合计的时候,三区政府算出Pälbar家族出了1万元而Pälchug Dampa Chödrag家族只出了3千元。他们自己没有去,而只是派一个叫Dampa Tharchin的去。Pälbar家族谎称是他们自己家的生意,
我们投入的本钱没有得到一点分红,可他们却说政府征收的税必须三家平分,丝毫不考虑我们应得的利钱。为了他们自己的两桩私家生意,他们打着赤江拉章的旗号,却谋取私利!最后弄清了,他们打算用我的本钱谋取自己的利益,并且没有说实话。可由于这是把物质与佛法联系起来的事,我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生意纠缠,只好让他们随心所欲了。
在Trehor的Zhitse Gyapön家族和Beri Monastery的财务总管Yatrug Tsongpön(这两人从前在拉萨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檀越)此前就一直给我写信,邀请我再次去Trehor地区。最后,我与一小群非常能干的人在那年夏天离开乡城寺,取道Tongjung Nang和Gämo Ngapchu牧场,到了Litang一个叫Dezhung Nakatang的地方,那里是个草原,那里花朵盛开的缤纷色彩还有人群、马匹和驴子的各种颜色会让你回头,让你惊讶得张大嘴巴!
我们穿过那片平原用了整整两天,只见到处是一群群移动的鹿群、羚羊等等,并且经过Nyarong各地(如Trom Tar),最后到达Trehor的Beri各地。到Beri 河的时候,Beri寺的Getag杜固仁波切带领僧人们列队来护送我们到了寺里。应寺里的众人以及前文提到的两位檀越要求,我给住地僧伽和这一地区各处的在家和出家者700多人,开示了菩提道次第Delam,做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怖畏金刚、棍利和大慈悲者大灌顶,和大黑天、法王、Sridevi 、多闻天王随许灌顶,还有Chamsing(Drubgyäl长生灌顶),以及其他按照要求做的口传和开示等。我在那里讲解了1个多月。
接着,我应Trehor Kartze Trungsar 仁波切邀请,去Trungsar 闭关处给仁波切阅读传授Gyälwa Wensapa和Kädrup Sangyä格西的选集,缘悲经集等。在该闭关处的云堂里,我还给积聚的许多僧俗人等(包括Kartze寺的僧伽)做了棍利大灌顶。有一天,应Kartze要求,我去给他们的大云堂和三个僧寮堂做撒花加持。路上,应Kyabgön杜固的邀请,我去拜访该拉章,傍晚回到Trungsar闭关处。当时该处附近住着一位非常著名的博儒Trehor Dragkar仁波切和Lamdrag 仁波切的前世(他是一位瑜伽大成就者)。我想去拜访他们。
可Dragkar家和Kangsar的前世Lozang Tsultrim互相不和,这让Lamdrag Kangsarpön的妻子十分恼怒。她应当很有权势,就连Trungsar仁波切和Gyapön Bu都害怕她、躲避她。这样,我就没得空看望他们。
Kartze寺有一座“本地护法庙”。有一天早上,我在寺前的寓所看见一层楼高的8尊帐篷大黑天佛像,十分有名,据说是Drogön Chögyäl Pagpa从中国回来后,在Yarlam建造的。然后,我又回到Beri寺。
当时Trehor Dargyä寺僧伽众多,权威很大,财力雄厚,但众人佛法知识贫乏,觉悟不深。因为大家埋头做生意一类的事情,大多数僧人忙于马匹、刀枪等等,真正修法的人很少。因为就连那些僧人也既没有法力,在寺中也没有权力,Gyapön 家的长老Chögyälu (他是Dhargyä寺的檀越),怀着一颗慈悲心,想引导那些和顺的僧侣们,就说我应当教导他们一点菩提道次第的教诲。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可他对寺里的众人说到此事,他们却说:“我们不需要那种花很多天时间的菩提道次第开示。许多僧人中风死了,我们需要做灌顶,治住行星的威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需要Kunrig仪式给死者做法事,我们需要做Kunrig大灌顶!”
Gyapön家的父亲失望透顶,于是便说我应当给他们做Kunrig大灌顶来遂他们的愿。当年帕绷喀金刚持第一次到Dagpo接受Jampäl Lhündrub金刚持开示菩提道次第,就是这位Gyapön家的长老供给的全部骡子当坐骑。他当随从的时候,Dagpo喇嘛仁波切把自己的一颗牙齿送给了他。他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还给我看那颗牙齿,我清楚地看到上面有一尊4臂慈悲者像。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念诵Jorchö(菩提道次第的起步修习法)。
按照Gyälu的要求,我接着从Beri寺去了Dargyä寺,在寺前面的开阔原野里,有人扎了一顶帐篷,我给一大群寺院的僧人和当地人,做了两天多的Kunrig大灌顶。虽然我事先没有打算讲授菩提道次第,却在灌顶的准备阶段进行了广泛的讲授。我还做了加持,从寺上层的云堂撒花。
然后,我到了Shitse Gyapön家,在那里住了大约2周。他们在神坛上放了观音菩萨佛像、完整的Kagyur 和各种身语义像等圣物。我在3天时间里,就像在Dargyä寺一样,做了广泛的加持。我给府库做了多闻天王丰足仪式,给当地一大群人开示了修心七要,最后做了长生灌顶。我经由Nyagrong各地返回,来到一个宁静的地方,只见上Tromkok地区的山边,绿草如茵,几条溪流潺潺流淌。我们停下脚步过夜。Gyapön 家的儿子Döndrub Namgyäl、还有Tsongpön Yatrug和他们的随从一直陪伴我们到那里。在此,他们要和我们道别回家,要求我教诫Draminyän长生持修法,我给他们做了简短的开示。
当天大约喝晚茶的时候,突然黑云翻卷,冰雹狂泻,同时,仿佛要把夜幕劈开的闪电发出剧烈的响声,帐篷内的红光摇摆不定。当时的闪电非常剧烈,仿佛地动山摇,好像要砸下陨石。我为神灵做了香供,为当地的神主供奉了朵玛,为8种世间神灵供奉了金酒、做了供奉,还念诵了防止冰雹和闪电的心咒。虽然我做了非常畏怖的观想,但无济于事。于是我用炽热的火燃烧了湿的粪便。立刻,就像幕布拉开一样,头顶显现了蔚蓝的天空,闪电和冰雹也偃旗息鼓,太阳也出来了。当晚大约半夜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马和骡子突然叫起来,挣脱了缰绳,四散逃走。直到天亮,才把它们收拢。
后来我到了Litang,发现有些老一辈的人说起嘉瓦仁波切Sönam Gyatso经过那一地区的时候,有一个本地的苯神用闪电击他。他们说起那里起来一场剧烈的风暴,当时我的前世也在场。
接着,我们到了Bum Nyag Tang,那是Litang一个广阔丰美的草地。Litang地方有一个人叫Washul Yönru,Yönru 指挥部所管辖的全部游牧群落都聚集在那里。Yönru地方的僧人们是格鲁派、萨迦派和宁玛派僧伽。他们的一个传统是扎一座汇聚帐篷,聚集在他们所谓的“我们自己的Yönru佛法”下,各派举行仪式都各行其是。所以,Yönru Rabgyäling僧众的官方喇嘛代表们包括Tromtog杜固都找到我说:“您的前世来到我们法会上,住了下来,与我们结下了佛缘。我们许多年长的男女居士和僧伽遇见过您的前世。眼下我们意外遇上是非常吉祥之兆,所以说法一结束,您就应当留下来,放松休息!”。
他们坚持要这样,所以,虽然我不能与他们长期在一起,还是住了大概2周,期间进行了汇聚,而且主要是格鲁派寺庙的做法。我给大约500名僧伽开示了杰宗喀巴的菩提道次地Nyamgur¬¬––Lamrim Song of Realization,按照鲁依巴派传统做了两天胜乐金刚灌顶,还做了三派之主杰宗喀巴随许灌顶。每隔5天,他们的僧伽就会举行曼陀罗供奉,依次修习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怖畏金刚和棍利。有一天我参加了他们的胜乐金刚修习供奉法会。他们的传承基本上与下密院的相同。他们有前任甘丹寺主持送给他们的锦缎香囊做供奉。我还给僧伽们做了一整天的供奉法会,散供了佛像。他们那里有两顶两层楼高的格鲁寺汇聚帐篷,每顶能容纳500名僧人还绰绰有余。他们安排了繁复的供奉仪式,虽然住持、喇嘛、杜固和格西们都坐在地上,他们用堆起来的毛毡和毛毯弄成座位,于是一切都变得舒心惬意。
前任诸位大士们过去到访过这个游牧的佛法群落之后,定下来这样的传统:会众举行仪式时只能供奉白色的食品,比如大麦糌粑、米饭和熔化的牛油,不准用肉供。他们坚定不移地保持着这个传统,就这件事就值得钦佩。
附近的萨迦和宁玛扎仓也应邀前来,接受供奉,并应邀讲授佛法,如读传佛经。我还应周围牧民的邀请,拜访了15到20座牦牛毛帐篷群落,做了加持,还按照他们的愿望做了开示。那些游牧民供奉了许多马匹,我竟然得到100多头!我们把马从它们家乡的草场带走,可它们夜里又跑回去,很难收留,于是我们就把它们卖给了那些牧民,用卖来的钱做基金,每年向格鲁派的Rabgyäling寺供奉。
接着,有些僧官听说我必须去Litang主寺,就过去专门邀请我。我们到Tubchen Jampa Ling寺的时候,只见列队的住持和学僧人山人海。应寺中僧众的邀请,我在大云堂里,做了华摩派大慈悲者灌顶,事先预备了1天,还做了Drubgyä派长生灌顶。我还在旧云堂里,给喇嘛和杜固们还有大约500名僧伽——包括Tsatag仁波切和Gozab仁波切,开示了菩提道次地Nyurlam––The Swift Path Lamrim,做了勇猛怖畏金刚大灌顶。
在Tubchen寺,我当主持,Tsatag Känzur仁波切做行师,Gozab Känpo做密戒师,我们一起给大约30名僧人主持了新戒和具足戒发愿。 我还在Gozab 拉章 给那位喇嘛的随从们做了Drubgyäl长生灌顶和杰宗喀巴三派之主随许灌顶。另外,我还圆满了许多僧俗人等的心愿,在Litang大云堂里做了大散供,并通过繁复的仪式向会众供奉了金钱。
在Litang镇,应嘉瓦仁波切Kälzang Gyatso出生地民众的邀请,我去了1天,给第7世嘉瓦仁波切金身还有一些身语义像做了沐浴和加持仪式并简短地与当地人结了法缘。我还应Litang当地Otog Pöntsang家族的游牧民众请求,去举行了昌盛与加持仪式,并按照他们的请求,给Pön Achö和他的随从们以及当地人、大群居士和僧伽包括Otog寺的僧伽做了各种教诫,比如观世音随许灌顶和长生灌顶。
Washul、Yönru 和Otog这3大游牧群落十分信仰佛法,多次念诵几十亿次观音心咒和几亿次缘悲经。这次他们也念诵了1亿次观音心咒和缘悲经、10万次普贤菩萨祈祷文和100次Nyungne 2日闭关斋戒等等。因为他们功德如此高深,因此非常多福兴盛,人丁兴旺,在到处游牧的同时証得了妙谛。
因为我事先听说了这些游牧民族有一个传统:如果请了一位喇嘛,就要宰杀一头羊大开宴席,我从一开始就特别说明:除了白色食品以外我什么都不吃;他们不必准备肉食。我去了Otog 地区的许多游牧民族所在地,举行沐浴加持仪式,应邀教诫佛法。
在Litang完成了这一切,我便往回赶,去Kampo Nä朝圣。Karmapa Düsum Kyenpa 在Kampo Nä居住了很长时间,获得证悟,Kampo Nä还是他始创的Kamtsang Kagyu传承得名的由来和时轮金刚(Sri Chakrasamvara)的重大朝圣地。我住在Nägo 扎仓上层的僧寮里,闭关了大约1周的胜乐金刚,然后用胜乐金刚本尊做了广大的灌顶。我还给当地的大约50名僧伽做了甘达巴派5尊胜乐金刚大灌顶。他们供奉了白银和一幅胜乐金刚画轴。我觉得那是吉祥之兆,便留了下来,现在还在拉萨、放在我身边。
我给僧伽们做了法事,有一天去朝拜一座叫Kampo Nä的山谷。Kampo Nä 这个名字主要来自那里的一块巨石,上面天然有一个“Ka”字。我去做了荟供。途中有一座陈列着许多勇士(他们都被勇士Gesar of Ling打败)使用过的武器,比如铠甲、箭、刀、矛、Gyatsa Zhälkar的刀、Yazi Kardrän等。Kampo Nä山谷的一侧是一座雪山,是Chakrasamavara所在地,周围环绕着诸神随侍的稍小雪山。 人一到达现场,就会神智清明,心态安详。我真想放松一下,呆在那里,却突然接到特别信使从Pälbar和乡城的Dampa家庭送来的信。
我们的三位商人伙伴已经从昌都回来了,带来了马匹、骡子和货物,他们人还在上Bumpa地区。他们走到Kangtseg关时(那是Ka村附近的难关),遇到一支来自上下Bumpa地区的一大队人马的伏击。4人被杀死,其中包括Pälbar家族的一名堂兄弟Tänzin和Dampa Chödrag的侄子Tarchin。匪徒还分别杀死了Pälbar家和我们的一头骡子,抢走了所有的货物。
因为他们没有报复那些仇敌,而且没有力量这么做,所以让我立刻去乡城。我立即动身去乡城。我一到那里,就见Pälbar Chödrag和Dampa Chödrag气势汹汹,跟我说了许多必须开战的理由。
我说虽然我们三方合伙当中有我的名字,但本应做个喇嘛,可如果先是到寺院讲授佛经和密续,然后,一会到西藏中部,就发动战争,就会在此生和以后诸生无所成就!所以,我请他们放弃那样的想法,放过那些人、牲畜和货物,不许他们打仗,让他们答应悄悄地放弃所做的战争准备。
我们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Bumpa部队伏击商队的原因是,先前与Dranag喇嘛在Tzetze寺开战时,乡城军队从Bumpa地区拿走了大批武器和食品,却没有做任何归还的承诺,而在大军队首的,就是Pälbar Togme。虽然Pälbar Togme病死在战场上,Bumpa人却没有放过此事,仍然对Pälbar怀恨在心。因为商队头人姓名中有Pälbar、生意是Pälbar家做的,他们对商队发动了袭击;好像他们并不知道我与商队有关联。
与Bumpa地区的战争逐渐减弱,双方举行了多次面对面的和谈,最后达成决议。Pälbar家族派出的一名代表Tändrong Sampel Tänzin和Dampa家族派出的Dampa Chödrag、我这边的两个人——秘书Gönpo和Ngaram Budor,找了个地方举行和解。
大家习惯称之为Zangdän、Jema喇嘛的代表Gowo Gönsar寺喇嘛说他们来到靠近Bumpa和Yül Lung 的Gowo Rong进行和谈,但Bumpa一方的人还没有打算阻止战争以免让双方受害,于是和会严重推迟,3个月后才达成明确的决议。
最后Bumpa人归还了一点点银子、几头老骡子和几件没用的衣服,与战争造成的重大伤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银子大多数给了Pälbar和Dampa家,补偿他们的人员损失,他们为自己的gau盒子讨价还价,因为那些盒子保护了武器、陨石金刚、左轮手枪等。虽然他们得到的银子和各种衣物应当与商队刚出发时他们贡献的数量相等,但是轮回和涅磐是同样的味道:分成3份,三方得到的都很少,因此大家都受了损失。另外,就像Jowo喇嘛Rakshita说的那样:
受了别人的欺骗,
错在自己骄傲淫荡的魔鬼
是恶业的刀枪害了自己。
就像他说的那样,不恭谦、静止、言行从众,是个魔鬼,能引火烧身。我们没有发动战争、从而杀人,就这一点,便使我大受鼓舞; 我对发生的事不大感到懊悔。他们两个抱着自私自利的目的,就像无数难以想象的灾难一样,这两个人受到敌人发出的雷霆般的电击,遭到惨败,等等。
大约这个时候,前文提到的色拉寺Me Pomra 康村 Beda Troti 杜固的舅舅Beda Tsultrim从拉萨来,假装是到乡城寺来筹款举行杜固的格西学位授予仪式,可事实是他在旧云堂里与上乡城的许多主要居士和僧人领袖会谈多日,谈的不是筹款办仪式,而是私下里与他们串联,让其支持他侄子、认可他是实“真正的”灵童。而且私下打算杀死我、把我逮捕、消灭或者除名。
有一个与杜固是朋友的,叫Tändrong Sampel Tänzin,被问到他说什么意见时,他立刻回答:“您必须弄清自己能否听任自己首领的摆布!我不知道乡城的人能不能起来支持他。如果他们能做到,我可以假装是个中立的中间人来保护你。因为我是赤江拉章的檀越,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当一群豺狼密谋的大恶行径暴露后,因为有证人(比如忠实诚信的Tsaka Lagän和Bali Kädrub)目睹了那些人从会谈场所出来等,并且秘密地把消息透露给我。当时我只有几名随从,正准备回西藏中部。我让几名聪明的僧人在我僧寮(位于云堂上部)门上加了几道栓。我们还在我卧室后面、墙壁和布帘之间挖了个能容纳一个人的藏身之处。寺院附近一些无私的人,比如Puntsog Dargyä,还有寺里的一些僧人,说到遭到攻击什么的时候,对我的随从们说:“如果你们能坚持一会儿,我们就会得到警报来支援你们!”就连我的随从们也做好了临时充当保镖的准备。
我请求三宝,供奉了诸护法,还从内心深处把自己托付给两条业果的定律:1. 业不作不得,没有造作的业力是不可能感果的;2. 业作已不失,而已经造作的业力永远也不会失去。
我静等了1个多月,用尽了各种手段,有10天左右的时间,危险的情形会爆发的征兆已经确定无疑,比如我僧寮外门的上栓断裂,横杆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谁弄断了栓、谁拿走了另一条栓。有一天黄昏,突然听到有人敲我们小院的马厩外门,有人在叫。我的一个随从非常害怕地问是谁,回答说是“Wangyäl”。 Wangyäl 是Pälbar Chödrag 家族的一个人,是Sampel Tänzin的亲戚。他说Sampel Tänzin刚刚得了一种中风,头部有一半麻痹,他来拿一些赐福药丸和香,第二天去进行保护和驱除恶鬼。
因为可能是我们一个檀越的家族成员Sampel Tänzin,我无法拒绝。我拿出来赐福药丸和香等,并且答应第二天过去。 仆人们比如Ngaram Budor 等都怀疑中间是否有诈,但从Wangyäl的动作和话语来看,我觉得他没有说谎,于是悄悄地觉得乐不可支。另外,我应当多次听过自己的喇嘛关于修心的讲解,却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因此“看起来像个满腹经纶的行者、阳光普照,实际上遇到灾祸时希松平常”并不是我的本意,因此我便放心地前去。
很快到了三昧耶断裂的地方。我对于灌顶和摩顶加持不想多发一言,因为对方是个外部的施主,一同前来的几个仆人和随从觉得非常害怕。我们到的时候,Tänzin已经起床了。他对我说:“您没有因Bumpa那帮人袭击商人进行报复,愤恨不平的Bumpa人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回应,因此我对您产生了坚定的信仰和尊敬。可因为我的信仰出了一点偏差,护法们便惩罚了我!” 他满怀后悔地忏悔之后请求进行沐浴和发愿。 在此之前,有一位Gorong地区的喇嘛告诉他必须由我对他进行三派之主随许灌顶;说这些无论如何都要给他做。 他对自己的恶行无法忍受,悔恨万分地哭泣,脸上流露出一直隐藏的东西。一如Ralo大士所言:
您给予各种金贵的东西,我却
像怖畏金刚一样解说Sadmukhakumara。
当时的情形就是那样的。第二天他稍微好些了,并且有20天左右的时间都慢慢起色,后来能来回走了。可接着,他又在他们家房子的楼上与Pälbar Chödrag 会面,一同吃饭喝肉汤,又像上一次那样开始谈论把我杀死的老话。
他又一次发了非常严重的中风,不能说话,当晚就死了。他们请求我第二天早去施颇瓦,我便回去做了颇瓦,并尽自己所能做了最好的请求、回向和祈祷。Sampel Tänzin 死了,他的支持者们烟消云散,像泄气的皮球,Troti杜固的随从们密度策划的东西也自动销声匿迹。
就在Sampel Tänzin中风之前,我梦见有人杀死了一头大牦牛。这是一个兆头,表示护法们很快会实施畏怒的行动。我做这样的梦不止一次。每当我梦见有一头山羊、绵羊或者牦牛什么的被杀死,不久以后,某个直接或者简接亵渎圣谛的人就会或早或晚被引到来生。
.
土龙年我28岁。大法会结束时,乡城的Treng分区一些村庄比如Rigang和Chagra Gang向我发出邀请,我便一个接一个地去那些地方,按照他们各自的要求和心愿在私人或者公众聚会上通过开示佛法与他们结法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hagra庙是第6世噶玛巴Tongwa Döndän 去住过一个冬天的地方。他在一个地方用一袋念珠砸过的地方,长出一棵菩提树。庙里还有一尊加持过的他的雕像和其他圣物。我在庙里住了几天,给大众做了长生灌顶,传授了6字心咒。
噶玛巴的佛法传承曾经遍及乡城地区,因此那里从前有许多不同的噶举庙,而现在这一地区的上下两地到处都是殘垣断壁。 当时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些仪式僧,会按照密续传承(叫“阿尼- Amnye”)举行护法和神像仪式。他们保留了当月10日向莲花生大士(Guru Rinpoche)供奉的传统、修习Bernag“黑袍”大黑天 [祖卜寺(Tsurpu)派护法] 还有Shingkyong Tragshä和Tashi Tseringma诸护法。 住在附近的Ngagpa修密者们全部聚集在一起,讨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灌顶和法传。
因此,我在Chagra庙依据嘉瓦仁波切Gendun Gyatso的本尊成就法,做了莲花生大士平安和怖畏随许灌顶,还依据Rinjung成就仪轨集,做了诸护法、Gönpo Legdän、大黑天Bernag、Tragshä以及五位长生姐妹Tsering Chenga灌顶。我在Chagra Padma家做莲花生大士摩顶加持时,主人供奉给我一把正在盛开的白色莲花。这是个意外的吉祥巧合。
当晚,我梦见有个黑色的人过来对我说需要重修那座庙。我知道那是诸护法的敦促,于是第二天就催促当地人重新修葺,在上面建一座小僧寮。第二年他们建了一座新庙,但没有建僧寮,而且许多年都没有建。后来,到木马年,僧寮建了起来。又过了一年,我从中国回来的途中经过Yarlam乡城,有机会在Chagra庙住了一晚。他们说现在可以理解我从前下命令要建僧寮的用途了:只不过是实现我从前的打算。附近的信众,按照“虚伪的喇嘛们”的说法,说他们一直想到会建这样一种东西,并且早就预料到了!
然后我经过上Ragpo和下Ragpo。Ragtö–Upper Ragpo有温泉,所以我呆了三天,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也是应当地民众的要求,写了一篇关于Tashi Lhakang庙尺寸和功德的文章。
我接受邀请去造访Dongsum所属的三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前任甘丹赤巴Jangchub Chöpel出生的地方呆了1周,在Dongsum五家族庙,供了10幅千佛唐卡给mitsän 即康村 家族的五个分支,那些唐卡从上到下自然排列,我还给僧俗人等做了大悲者长生灌顶。我还去了前任甘丹赤巴在Chuzang Monastery的僧寮,做了灌顶,给那里的家族成员不少布匹和其他东西。
我们又一次来到乡城,除了茶功(Chagong)上乡城的Troti杜固家还有Söpa和Pälge仍然对我心存偏见、没有邀请我的一些家族,我不辞劳苦地拜访了很久以前和最近曾邀请过我的上下乡城各个村庄的人们,去讲经说法并举行法事,满足了他们的全部心愿。但正如《智慧枝干》(Sherab Dongbu–Trunk of Wisdom)所说:
“天体之城,无人穿衣,
洗衣工还有什么可做?”
就这样我呆在那里,但并没有什么重要目的与好处。不仅如此,而且像《本生经》所说的那样,
心生嫉妒之人,
无法忍受别人取得的成就。
他们怀着仇恨,做事盲目虚假。
当时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到别的地方去。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当年就回到西藏中部。Zeu Dru寺的Gangkar Lama 仁波切来过一封信,说我在4月15日不要离开乡城,否则性命会有很大的危险。同时,我还必须去上面所说的村子如Chagra Gang、Ragpo及Dongsum,并且动身的准备也做得不好,于是行程推迟了。
这期间,一些从拉萨返回的僧人和商人说,他们到Markam Gartog的时候,由于同乡城有过冲突,心里怀着恶感,Markam诬告他们无端对自己征收了惩罚性税款,于是他们与Markam Dapön Shelkar Lingpa的边境警察有法律问题待解决。那些乡城僧人和与他们结伴同行的人遭到拘留逮捕。他们没收了马匹、骡子和货物,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Pälbar Lagän Chödrag仍然对已故的Sampel十分怀念,对我们心存恶念,要阻止我们去拉萨。他终于得以拖延了Shepa Pagtrug等僧人、商队、Drogdog Chödrag、Drodog几个最强有力的人还有我们去拉萨,Markam Datzong举行了谈判,要求立即释放僧人和商人们,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虽然有些人包括我提了意见和建议,但Drodog Chödrag和其他人都坚决主张必须推迟行程,直到争议得到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已经决定今年去拉萨,我们可以在首府向嘉瓦仁波切请求,我们已经发出了请求。
因为我不接受推迟行程,Pälbar Lagän and Drodog Chödrag 策划了一场邪恶的阴谋,要在Yarlam Drodog 会合,准备杀死我,取而代之,他们正在召集人马等。有个叫Pälge Gyagser Yapa的僧人得了甲状腺肿。他曾经和Troti杜固的叔叔一道,接受了我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佛法和大威德金刚灌顶还有经文讲解,他曾发誓要进行长修,可有人听他说:“赤江一行人能轻松没有障碍地到达拉萨吗?我感到好奇!看看他们表演吧!” 后来他的甲状腺溃烂,好久都奄奄一息。他叫人给在拉萨的我送了一封信表示忏悔,但已经无可救药,于是离开了人世。
上文说过,当时情况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危险来自四面八方。于是Lutag Tashi Tsongpön、Nyanang Puntsog Dargyä、Shab Gyatso Nyima和主要军官们带领1千名骑兵,要求护送我们一直到Markam,好让我们经过Drodog秘密地直接赶路。要是他们护送我们到达Yarlam,我们肯定能轻松安全地通过,可我想到护送官兵会与Marlam军交火,这样一来肯定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于是我打算从Nangzang寺一带往回绕道。我向Nangzang写了一封密信,可他们答复说,因为有人保障我安全通行,我应当与护送队伍一道走。
这封信至少起到了决定我行程路线的作用,可Drodog Chödrag知道了这事,于是捎了一封口信,让我稍微多呆一段时间,好让年轻的僧人和商人们也能在从Markam出发时得到护送。信里还有一封信,用带威胁的口吻说:“我们本来打算让你经过Nangzang寺过来,可你来的时候喇嘛已经离开了。以后我们要谈这个事。”可Nangzang却说:“以后您不管做什么事,我们的喇嘛会在您来的时候负责”等。这样,由于当时情况极度危险,取道Nangzang再次显得可行了。
虽然我们已经决定6月3日从乡城动身,但直到2日我们还没有决定走那条路线。那天,我冒着风险、也是为了多一条路子,举行了kangso仪式并进行了供奉和占卜以确定到底取道Drodog、Nanzang还是采纳其他意见取道Litang或Gyältang,看哪条线路最佳。我用“卷纸团”的占卜方法,结果显示,取道Gyältang最好。于是我们私下做了这样的内部决定,可对外却继续声称会经过Drodog向北走。
3日凌晨,我们动身之前只告诉寺里的上层我们会经由Gyältang向南走。大家严守秘密,有些前来随行的僧人和卫队已经朝Drodog方向走了,只好返回向Gyältang走。那天我们的随从们从乡城桑培林寺动身。当我们到达寺前大桥另一边的大山旁,我回想当时的艰难情形,出于不太无私的考虑,觉得自己终于从黑暗的地牢中获得了解放。
虽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再去那里,但在回忆的时候却想起自己把垫子和班智达帽放在那座寺云堂的法座上;回想自己所做的事,觉得是个凶兆,于是想到:“很可能要再次遭遇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后来,在木羊年、我55岁时,从中国途经Yarlam返回的时候,按照嘉瓦仁波切的指示,我只得去几个前藏南部的几个格魯派佛寺,包括Litang、乡城和 Ba。
重返乡城是与上次事件互为缘起的例证。我已经斩断了业缘的丝缕——既有善业也有恶业,但却无法斩尽。由于自己承继着甘丹赤巴Jangchub Chöpäl流派的脉络,我再次复苏了乡城寺一带的政治与佛法的生机,人们以为我长期以来努力用自己的身语意在许多方面保证这种生机不再恶化,而是不断增益。由于这个缘故,大多数僧俗人众都爱戴我,对我发了三昧耶誓。可是,就像Tukän Chökyi Nyima说过的那样:
你教他们佛法,他们报以犯罪。
你对他们仁慈,他们以怨报德。
你信任他们,他们报以欺骗。
末法時代的人们,难以与共!
还有,Chöje Zur Karwa Legshä Tsöl也说过:
纵使给人巨大恩惠,
无论高低贵贱,一视同仁,
许多人毫无羞愧,报以污泥;
让我心生放弃之念!
正如他所言,有些人不能以德报德,他们的欲望无法满足,他们想要食物堆积如山,却不想要山;他们的信徒,无论早晚都使出各种各样的招术,要把我的脑袋放在香油磨里,可多亏了上师和三宝的慈悲以及业谛的威力、和名为“多杰”的护法长期如影随形的护佑和无所不在的及时出手,我在一个月明天青的夜晚,得以摆脱恶缘的缠绕,绝处逢生。
那天傍晚我离开乡城寺,在Ragtö Tashi Lhakang过夜。我经过Wangshö和Gumnag等地方,到了tang Sumtsen Ling寺,在那里住持和列位前任住持、喇嘛、杜固还有官员以及众僧人排成金色队列,举行了繁复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下榻在灯火通明、有窗户的僧寮,位于大云堂的上方。我在宽大的云堂里,给大约2千名僧人讲解了菩提道次地Nyurlam,并作了13尊怖畏金刚灌顶。应八个不同的康村当中的每个如乡城的邀请,我对其讲经说法,并按照其各自的愿望做了灌顶。我在那里待了大概3星期。
那段时间我与Gyältang Tongwa Lhakar仁波切的前世见了几次,他60多岁。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进行了一些考验,问了许多经文和密续方面的问题。我从未卡壳,这让他很高兴,于是参加了我讲解《菩提道次地》的课。此后每年他经过前藏的时候都会给我寄一封信,里面装了一些金子,直到他去世为止。
我到拉萨后,帕绷喀金刚持告诉他同在寺中的下一届同学Lhakar仁波切我在学法方面必有大智慧。另外,我还接受了Panglung拉章和其他一些拉章比如Kagyurtsang的邀请。 Gyältang Sumtseling寺是在5世嘉瓦仁波切在世时修建的,由于该寺受到嘉瓦仁波切的檀越Narim和当时中国皇帝的重视,因而里面粗大的柱子间悬挂着许多人物(如Gushri Tänzin Chögyäl、Desi和历任嘉瓦仁波切)唐卡,其文件印鉴还是用金线刺绣而成的,就像供品在那里摆放一样。据说这些唐卡分属8大康村,各有其传承,就像每种教派传承修习经文和密续时都有其独有的唱诵旋律,而汇聚在一起时却又能够形成一个和谐整体。Gyältang寺的传统强调其成员必须摆放姓名和垫子。于是,我在大會时和果源(tob kung)乡城康村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名单,象征性地作了供奉。
接着,我们经过Gyältang、上Tang Rongpa Tangtö和下Tang Tangmä,到达Drichu河。我们沿陡峭的Nyeri峡谷往下走了一天,到达Drichu河岸边。众人备好木梁将其捆绑在一起,做成一块平面木筏,上面没有一样东西支撑身体,大家惶惶不安地过了宽大的Drichu河。
我们沿着河岸和及其崎岖不平的峡谷走了两天,到了Kontserag村(又叫Pomtserag)。第二天,Tratang 仁波切的前世和当地人穿着盛装在Yarlam Shipäl Retreat与我们会合并加入队伍。我们到达的时候,Döndrub Ling寺的喇嘛、杜固和僧官列队欢迎。我在Ludrub 拉章呆了几天。
现任杜固Ludrub的前世当时只有七八岁。我向Tratang 仁波切、众喇嘛、杜固和整个僧伽做了五尊胜乐金刚大灌顶(甘达巴传承)。
我在Jöl Dechen Ling寺Zamdong拉章呆了3天,给僧伽做了“三家大尊主杰宗喀巴”随许灌顶,还根据现场需要做了其他的讲经活动,比如做长生灌顶等。
Zamdong仁波切的前世是一位佛法良友,我曾与他一起在拉萨听法。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当时正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给大家做长生灌顶,却被当地的坏人从Pari树林里开枪,死于枪伤。
接着,我们经由一个叫Jöldong的村庄,穿过一个小关口,在Tso Kamka湖边呆了三四天。Gangkar喇嘛家里的人和Zeudru寺派来的护卫到湖边迎接我。乡城的护卫于是往回返,朝Nangzang的方向走去。
我们一行穿过Tsala关,到达Dranag寺。我给那里的僧伽(包括Nyira杜固)讲经,比如口传和解说《普善德根本》(Foundation Of Good Qualities)。
接着,我们先后经过Chusumdo村和Kapo Butsa村,到达Zeudru寺和Gangkar喇嘛家。我们在那里呆了10多天,全家人对我们非常殷勤周到。我们与仁波切的随从非常熟悉,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给该寺的僧俗人等和当地人作了大悲者大灌顶,而对纯粹的僧伽则做了十三尊大威德金刚灌顶。
有一天,喇嘛全家为我举行了大型的长生荟供法会。喇嘛告诉Ngaram Budor,自己用天眼看见我是莲花生大师,这让他想起自己与我数次在前世结缘的情形,比如我曾出生为大译师毗盧遮那佛。此时,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瑜伽师用天眼什么都有可能看见,但这并不表示就是看见的人物!由于他与我有清净缘并且笃信不移,而我只能说我没有这种種性的丝毫味道,甚至没有做过可以声称自己给这位喇嘛托梦的经历。我还给给喇嘛仁波切作了大规模长生荟供法会。
我在乡城的时候,芒康将军Shelkar Lingpa想抢走Gangkar喇嘛家的南面盐坑,于是他派出了第4军500名士兵,还有芒康各地的地方武装,突然悄悄地包围了喇嘛在Zeudru寺的家,向他家发射了许多炮弹,还用枪向他家涉及了很多次。就在军队到来之前,Gangkar喇嘛梦见一只大鹏金翅鸟从Dragkar Tzong飞过来,给他几粒长生铁丸,好让他吃了刀枪不入,还给了他一只打开的珍宝盒。
他说出来几个僧人的名字,大鹏金翅鸟让他给每人一颗,让他们每人拿一把刀,把敌军赶到寺下面山上的佛塔边,并且让他们无容置辨地回去。前面所说的大军就像一群被狼追赶的羊,把衣服、食盒、鞋子等等丢了一地,落荒而逃。敌军士兵发射的一颗迫击炮炮弹还落到喇嘛的住所,但没有爆炸。到现在还能看见那颗炮弹呢!
放置珍宝盒和铁丸的房间充斥着草药的香气。喇嘛仁波切让我们看那只珍宝盒,把它打开,还给我们铁丸。至于珍宝盒,里面装满了大约五指宽、好像“龙屎”一样的东西,而盒子本身却只有三指宽,而且四周还有各种神像自己往上升起。盒子装得满满的,快要溢出来了。虽然喇嘛给我的随从和乡城来的人每人一颗铁丸,但铁丸每次数量都立即增长,都快要溢出盒子,撑破了纸板箱,然后就停止增长。真是神奇的景象,让人生出坚定的信念。
离开之前我请喇嘛仁波切就几个问题(包括我身语意行问题)提出见解。他说,他在以前做过的梦里,清楚地看到有一座大云堂,里面有一座很大的旧法座。有一些人围在前面急切地建一个新法座,这时一位相貌不俗的僧官、好像是一位宫内大臣到了。他一到那些建新法座的人就不见了。那位僧官的仆人身穿红色的外衣,他彻底打碎了新法座,扫除了垃圾并把所有人都赶走了。他说:“主人,这些恶缘肯定不会加害您了。看来嘉钦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声如洪钟地说:“这我可以保证!”
后来,水猴年在拉萨大法会上,Troti杜固的一个主要人物——乡城Pälchug Dapön格西患了致命疾病去世了。7天后杜固本人也生病去世。就连前藏那些从前参与错误的谋划和活动的人都遭遇了各种遭难,不久后都丧命了。
另外,Gangkar仁波切在识别灵童或是有人想找到丢失的东西时,会在梦里寻找线索,或者闭上双眼入定一会,然后清除地指出地点和位置、村庄、屋门朝向、哪家还有姓名等。他的预言总是很准确,总能让人找到要找的东西,我自己就亲自经历过几次。
不仅如此,我第一次出来到乡城的时候,喇嘛已经满头白发,可后来我回到Yarlam时,他的头发却又变成黑色。他对13世嘉瓦仁波切信念坚定,期愿很深,总说只要第13世嘉瓦仁波切在世,他就不死。后来听说嘉瓦仁波切辞世,他立刻说:“好了,我该当老僧人了!”他有点水肿,随后就去世了。
他把侍者们叫到跟前,大家一起念诵完心经以后,他说了一句“密门”咒接着就听见一声很响的“扑!”声,然后就去世了。这些事例清楚无疑地表明他达到证果。他除了修习上师荟供、大威德金刚、马头金刚密跡、“一故事摊佛塔”等传承和金甲衣护法,还修习许多本尊和护法,并且遵守其既定传承。
我们离开Zeudru寺,应4世Tzongpön Tai Jidrung Korpel邀请,经过Markham, Lhadun, Goshö, Pomda, Tsang等地去Tzongkhang。我在那里给Ku-ngo Tang-chäl和Özer寺的部分僧伽以辛都拉(Sindhura)金刚瑜伽母祝福,还给僧俗人等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
我应Markam Sasung将军Shelkar Lingpa邀请,去军营做了长生灌顶。Özer寺得到重建,从其旧址搬迁到Gartog上面的一个地方。我应邀去举行灌顶,同时还念诵佛经。
接着,我接受了邀请,去了Kyung Bum Lur寺,专给那里的僧伽做了13尊大威德金刚大灌顶。
路上我们在Ribur寺歇息了一晚。寺里正在修建一座立体Gyusamaja曼陀罗。他们对建筑的一些问题存有疑问,我做了解答,于是在一些他们需要解答的话题方面与他们有了法缘。
我在Chagna Mutig(掌珠)寺盘桓了两天。那里的众僧当中有一位曾是拉萨Tängyäling扎仓的羌母舞蹈(Cham)大师。据说他在羌母舞蹈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有一天他们表演了羌母风格的大黑天、法王、吉祥天母和黑帽舞等。那情景就像从前的Tängyäling Demo Gu Cham。
我们穿过Sampa Dreng Dachu河,相继经过Tsawa、 Rong、 Dugda、 Tzogang Sang Nygag Ling、 Uyag、 Tsawa Kochen Tang寺和村庄、Pangda寺、Wako Mar-ri、 Zhabyä Zampa、 Lhotzong Zhitram寺, Tzito寺、 Shodo寺、 Poti寺及Lhatse寺。我沿途在人们的要求下举行各种灌顶、嘱累、讲解等。我们最终到达Chagra Pälbar,呆在那里,我应下密院 Ngagram Ngawang Chöjor的要求,向该寺僧伽讲解和嘱累菩提道次第简编(Abbreviated Lamrim)。
那里曾召唤过一位神谕,名叫Gönpo Tsedü Nagpo,而Ngaram Ngag Chö带来了他的预言。护法神降神到神谕的体内,神谕自己左手拿着一只鼓,右手用一根棍子敲打。同时,我们在把护法神召唤降神在神谕体内时,一个人抓住鼓,神谕则端坐在法座上。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讲他用右手敲鼓的来历,他对后来的修习所作的预言有些得到了应验。
接着,我们穿过Shargong关,到达Ari寺。我们会见了Ngaram Dampa的亲戚们并互赠礼品。我们离开Ala Chag 寺,在到达Dotug前,名叫Namgyäl Dorje的大厨有一天早晨走了,从一个陡峭的狭道跌落下去摔死了。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天做颇瓦法,进行回向祈愿,然后焚化了他的尸体。
那天晚上我们经过那个关口,先后经过Lhari Go、Kongpo、 Gyamda等地方,到达Özer Gyang,在那里遇到了Gadän Dokang 康村及Samling Mitsän的代表们,他们随后护送我们。Dokang 康村事先为我们住在Tsunmo Tsäl 寺做好了准备,我们在那里呆了1天,在度津扎巴坚赞的塔前作了供奉。很久以前就众所周知的是,装有度津仁波切舍利身的塔在Tsunmo Tsäl寺,同时,由于必须对保存舍利身的地方进行修葺,管理该寺的甘丹寺 Lhopa Gyälsä 杜固及 Dokang Geshe Chödrag让我过去举行水供法会(argha¬–water–puja)。我们把它打开时,发现放置的圣物中有一只木盒,里面的圣体完好无损,还长了一些头发!圣体包在一新一旧两件袈裟里,前面放了一只很古旧的钵,好像里面装满了水果。戒淸净的香气充满了很大一片地方,这验证了我在寺里的时候Chödrag格西说的话。
我为那些法会和供品等做准备而稍微推迟了行程,但在当年10月初,我非常愉快地回到我在拉萨的僧寮。重逢恩师Gän Yongzin 仁波切、Sherab仁波切格西和其他人,仿佛见到了奇珍异宝。大家在快乐祥和的气氛中举行了节日般的聚会,大家日夜守在一起,谈论着彼此分别后发生的事情。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亲戚过来看我并表达了美好的心愿。
我按照惯例在罗布宁卡宫的阳光寓所(Sunlight Residence)与嘉瓦仁波切进行返回觐见,是在Jangchub Gakyil的山峰寓所(Peak Residence)举行私下会见的。我用头顶膜拜了他的莲花佛足。他是一切有的皇冠之珠,向他供奉了代表身语意的tän sum曼陀罗、一烟供金子,1千块中国元和几件前藏的土产。他提了许多关于前藏局势的问题,我毫不隐瞒杜撰地做了回答。
然后,我去Chusang闭关处拜访帕绷喀金刚持。他的曼陀罗面孔,比耐心地擦拭了100遍的、至上许愿珍宝都意味深长。我看到他的一刹那,便躬身跪拜,还供奉了金银等物。在与他进行的漫长会见中听见他的声音,感到无以言表的快乐和安慰。
Chone 喇嘛仁波切 Lozang Gyatso Trin Pälzangpo当时也在Chuzang闭关处。我去拜会他,后来凡是他讲授佛法我都去聆听。
11月初,在去甘丹寺的路上,萨济寺扎仓来了几个僧官在新建的Bönpo寺(位于甘丹寺下方)迎接并护送我,其中有住持的代表、Dokang官员和Lozang Dargyä。我们从Nyarong关的关口向下面的集市走去。从那开始,萨济寺的僧伽列成一队,还有萨济寺和江孜寺的住持、众喇嘛、杜固还有僧官,都手捧佛香一直簇拥我到Dokang 康村的大堂,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油炸食品摆的宴席。我受获了寺里的管事会、列位扎仓、康村、Mitsäns等,许多人群和个人上来向我所作的致敬、奉献的哈达,等等。
为了庆祝我们一路行程、还有呆在前藏以及顺利返回虽然历经艰难,却安然无恙,我在甘丹寺大众會期间供奉了两遍茶还有一次面汤,给每位僧人1份烟供和5 zho银子,外带一袋粮食。为了向大家普遍供奉,我安排了供养一年的tam。
我在萨济寺扎仓向众僧供了两道茶和热米汤。我向僧众供奉了长时休行小地毯。当时共有18排僧人,每排都很长,每位僧人都得到一块金质和莲花图案的小地毯。至于住持、喇嘛、领诵和仪式助理,我供奉了方形地毯垫,每块都有精致的软毛,四周有猩红的图案。我还安排了每年供奉一tam。
在江孜寺扎仓时我供奉了两道茶、一道汤,还给每位僧人发了3 sang银子,还每年供奉一tam。
在Dokang 康村时,我向大会众供给了茶和米汤,给每位僧人3 sang银子和1袋粮食。大荟供时,我向4根大柱子供奉了旗幡(头上用铜和金刺绣了猫头形状)、几箱精美的俄国玫瑰锦缎和多彩尾旗、两大箱加粉的香,一个吉祥宝幢还有1 tam。
我在Dokang Samling Mitsän、 Serkong 康村及Serkong 康村 Mitsän时都向那里的僧人供奉了茶和其他供品。
我向甘丹寺做了年度供奉后,为Marlam Dechen Sang Ngag Kar寺做了法事,还向我母亲和Gongko家族的其他人进献了礼品。在贡塘,我做了一整天的法事供奉,还在Chötri扎仓 and Zimshar扎仓分发了供品。我还邀请了我出生大神Dragshul Wangpo and Nyima Shonnu主神及其随从的神谕,做了感恩供奉,并把它们供奉在我在拉萨的僧寮中。
我29岁时是土蛇年。我在大法会上做了茶供,总共向全部僧伽分发了3 sho银子。满临祈愿大法会结束后,我还在哲蚌寺及色拉寺、上密院、下密院及Chuzang闭关处的大众会上供奉了茶并分发了其他供品。在上密院我供奉了专门在乡城做的150顶五佛灌顶冠。
那年在Chuzang闭关时,我受领了帕绷喀金刚持讲解的上师荟供和大手印本经等等,再次受获了对大威德金刚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修习法的讲解以恢复著述的法力,并有幸聆听了他讲说的众多佛法。
我30岁时是铁马年。为了新开设大威德金刚修习堂会,和振兴已经衰落的甘达巴胜乐金刚修习堂会,贡塘拉章的军官Magdrung Kälzang让我施行大威德金剛和胜乐金刚大灌顶。当时我得了一种发冷的病,但Magdrung Kälzang的催促不好推辞,便在当年4月初去Guntang做了灌顶。这一来加重了我的病情,来回穿越Tsangchu 河等,使发冷的情况更加严重,最后得了风湿症,不能出门。当时情形很艰难,我一直不能出门,一直到11月初为止。
那段时间甘丹江孜寺Tridag仁波切不断来我的僧寮做清洁仪式,和赎买仪式,以驱走恶业,还再次给我做了智慧大鹏金翅鸟随许灌顶。他建议我说闭关会好些,我便闭关了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大鹏金翅鸟,有绵羊那么大,从天空飞到我僧寮的顶上。有人把许多青蛙倒进一只盘子里。我用一块布把盘子蒙住,抓紧布角,用左手绷紧布。盘子里的青蛙往上蹦,让布鼓起来。我用右手轻轻掀开一点向下看,有两只青蛙蹦了出来,但其余的青蛙都被挤死了。 青蛙粘在布上,背上露出红斑。我估摸那是一个征兆,表明魔鬼的魔力已经得到纾解,在Shelkar Doctor Jigme和Chagpori的医学老师Kälzang-lag共同看护下,病因慢慢消除了。我差一点被死神的信使带走!
Tri Dagpo Ngawang Tashi的转世Tridag 仁波切也在佛经和密续方面学识深厚。他不仅懂诗歌、语法、梵语等,而且谙熟密续仪式的修习法,包括曼陀罗的大小和颜色。他还在唐卡绘画方面的知识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他还受获过Serkong金刚持和帕绷喀金刚持等许多尊者的许多灌顶、传授和指点,但从未有“我太棒啦!我是大学者!”这样自高自大的想法,从来没有像一个平庸的僧人显示自己那一点知识、在高山顶上挥舞自己的旗帜!他说一个含蓄内敛的人,把锋芒藏了起来。仁波切和我都曾皈依过同一个上师修习三昧耶戒,我们也经常在一起。但即使我知道仁波切受获过Serkong 金刚持口授的大量噶当派密传(比如有关一个老妇人来拉萨但看不见Jowo菩萨雕像这个比喻等),可正当我想请他口传噶当派密传的时候,他却生病去世了。
我的侍者Lhabu的父亲名叫Tashi Döndrub,曾当过很多年Dechen Pur 拉章的管事,那纯粹是出于仁慈。他也于土蛇年因病去世。他在立遗嘱时,让他的小儿子Päldän Tsering也要像他们一样加入拉章。所以,那年冬天,他从游牧的草原来到我的僧寮,还带了一些牛羊和护卫。不久,我教他识字诵经。他还很小,于是我让他去拉萨东Nyarong 的Lhaje Rigzin Lhundrup 学习文学。常言道:
非常幸福的时候不要溺爱,
极度悲伤的时候不要逃避,
你可以依靠什么样的业力?
仁爱之心是最忠诚的仆从!
这个Päldän Tsering从前当我的侍从对我照顾得很周到,现在继续无私而且身语意都不知疲倦地照顾我,他成了我这个老人晚年唯一可以倚靠的“拐杖”。
我31岁时是铁羊年,金刚持喇嘛讲经说法几乎每场我都去,无论大小、不管是在Chuzang闭关处还是在Tashi Chöling的闭关处;我还受获得了Tsänzhab Tagdrag金刚持作的密集金刚、智足大阿阇黎派文殊金刚和阿底峡派世自在大灌顶,还有一些阅读传授如怖畏金刚佛法Ra and Pä卷、大黑天集的“母经”,还有关于黑甘奈施的“子经”。
那年秋末,乡城寺及其所在地区的代表、Upper Chagong大会众官Pag Ge Lozang格西、和Pagpo(属于Treng一边)的Butsa Gelong Tänpa Namgyäl都来邀请我到寺里去。
我32岁时是水猴年,中国军队从Domä的Ba来袭。保护Domä的政府军无法抵御,从而Markam直到Bum关口的土地沦陷,等等。冲突蔓延到首都的危险性极大,于是政府只好请英国政府给我们提供武器。
我那年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Chuzang闭关处,听了金刚持喇嘛很多的讲经说法,比如他关于怖畏金刚4业轮的著述等。那一段时间在休息时我还做了几次本尊心咒念诵闭关。
那年10月,甘丹赤巴色寺杰Lawa 康村的Lozang Gyältsän圆寂。虽然我没有收到他的管事特别邀请什么的,但至尊第13世嘉瓦仁波切却在罗布宁卡宫决定召唤我去协助。我们赶到的时候,有人告诉嘉瓦仁波切的首席助理Kuchar Tubtän Kunpel Pebgo说我必须去准备和清洗头一天圆寂的甘丹寺Tri仁波切的遗体并举行火化仪式。
我匆匆赶往法座在Purchog拉章的僧寮。 我到达的时候,Namdrä Lobpön Kuzhab Sönam-lag还捎来至尊嘉瓦仁波切的信,说我和他知道遗体安葬仪式的所有程序,我俩就应当去做这事;Purchog杜固仁波切必须十分注意观察,以便为将来着想而获得传统法事的经验。后来我回想这个情节,觉得宗座13世嘉瓦仁波切有特别的天眼通,预知自己第二年会过世,Purchog仁波切和我们俩要去为他的珍宝舍利举行同样的仪式。
按照他的意图和要求,我们给法座的舍利做了一整天的沐浴仪式,然后将其火化,举行了自灌顶等仪式,然后在帕绷喀闭关处把遗体火化。我担任金刚上师,按照Tukän Chökyi Nyima经文的说明举行了仪式。Purchog也在,他非常认真地观看了整个过程,从举行沐浴仪式一直到最后,无一遗漏。
我33年是水牛年,大法会结束后,在甘丹寺修习Tagtsä时,第13世嘉瓦仁波切来到甘丹寺。我不敢在拉萨休息,便直接去了甘丹寺参加正在萨济寺举行的大威德金刚仪式。在这当儿我在清光僧寮法座室私下晋见了宗座。他问了我一些讲经说法的事和甘丹寺修习供奉的情况等,我对从前的传统做法作了汇报。嘉瓦仁波切到访甘丹寺后回到了拉萨。
我在甘丹寺的时候,在接受推理培训时的辩论伙伴一直是Pukang Geshe Ngawang Lozang,他是3所佛教大学当中最优秀的一名学僧。我和他同受三昧耶戒很多年。我这次还在甘丹寺的时候,他病在自己的僧房里,我还没回到拉萨他就圆寂了。没能在他辞世之前再见他一面,我感到无比失望和遗憾。从此后我替他回向了许多善根。
夏课结束,我邀请帕绷喀金刚持到我在Chuzang闭关处的僧房,进行17尊大黑天随许灌顶。正在这时,罗布宁卡宫派来的一名特使带信,让我次日早晨去罗布宁卡宫。
我到的时候Kuchar Kunpel Gyükay Pebgo已经接到乡城寺和当地递交的一份祈请文。前藏的僧俗人众请求我给个主意,好对我突然离开前藏之后出现的心神和俗事方面的混乱情形进行驱除。还有情报人员获得的情报必须转达,是关于中国方面企图入侵并为此做准备的事。他们还对于怎样举行仪式提出了广泛而详细的询问。因为年内我无法准备动身,只好请求把行程推迟到次年,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立刻做准备。
当时还有遗留下来的3场随许灌顶和大黑天密语言需要在大黑天法会上受获。后来我听取了Nalenda Kyabje Zimog仁波切的讲授。
虽然我打算去前藏并派了乡城大会众的Lozang格西去印度采办必需品,但当年10月13日,13世嘉瓦仁波切入了法界。从事讲法的僧人Purchog Jamgön Chogtrul、Tsänzhab Tagdrag Drojechang、Tsänzhab Sera Mä Kongpo Gyälwang 杜固、Sera Je Hardong Keutsang 杜固、至尊林仁波切和我还有两名Namgyäl寺来的小僧人去作必要的法事,比如住持伴随珍宝舍利的仪式等。为此,我去前藏的行程推迟了。在把珍宝舍利安放在仆从宫顶层的Sizhi Pälbar寓所时,我们主持了相应的仪式和法身沐浴仪式,还开始每周供奉食盐,等等。
过了几天,所有的高级侍从如Kuchar Tubtän Kunpel等还有医生Jampa从西藏的大会赶来,对造成嘉瓦仁波切圆寂的病情还有他的医疗情况问了许多问题。最后,监禁了几名官员,Tubtän Kunpel Kongpo和其他几个人被流放到各个方向很远的地方。
12月,嘉瓦仁波切的珍宝舍利被运到布达拉宫东边的甘丹寺光明寮。从那时起直到金塔建成好安放舍利大概经过了1年,在此期间每天都举行成就仪式和向舍利供奉。我们按照新摄政Ratreng仁波切和政治部长Yabzhi Langdun Gung下达的指令,确定了舍利塔的规制,还为把供品放在塔内做了所有的准备。
因此,在塔基的布上标注塔的尺寸时,标注得比5世嘉瓦仁波切舍利金塔(位于布达拉宫宽阔的东侧)下方布上标注的尺寸高了1腕尺。后来,Ratreng仁波切找到杜松木做直插在塔中的长生柱,竟然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长度正好等于从顶到放置舍利瓶的莲花座的长度,简直恍若天成!
说到一般的舍利塔轴心长生柱,虽然必须树在“十功德莲花”上,但在举行仪式把长生柱放在“无垢双尊”曼陀罗上时,“无垢双尊”曼陀罗放的高度位于舍利瓶垫和莲花座之间,长生柱底座必须放在曼陀罗顶部;我们遵照的是这个旧制。
我34岁时是木狗年。2月16日,我正在给珍宝舍利做法事,我的僧寮管事Rigzin事死于中风。所有法会和安排的事宜都必须由我亲自和我的侍者Lhabu操持。正如前文所说,我已故的管事智商很低,命运很差。他一直缺钱少粮,衣食无着,有时甚至要到村里向邻居借糌粑,春末向放牧的人预借。副执事有许多牛粪生火,还有空黄油瓶和柴禾,于是我们就这样艰难地过了几个月。可虽然我和Lhabu一无所有,因为我们能力很小,不能冲破封锁和招来好运,但凭着无上三宝的赐福和法力,情形一年年好转,开始变得吉祥,我也有机会修习资粮、供奉和布施僧伽,好像我有一口井,源源不断地向外出。
那一年Tsipön “财政部长”Lungsharpa Dorje Tsegyäl和Kalön Trimönpa Noru Wbangyäl为控制政府而争吵得不可开交,双方各有支持的僧俗人等,他们为各种问题争斗不休。最后,Tsipön Lungshar一派被逮捕投进大牢,4月8日,在布达拉宫下面的刑罚室里,他的双眼被抠出来,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一些同事也被流放到很远的边境哨卡。
嘉瓦仁波切在世时,由于他的慈惠,Tsipön Lungsharpa和嘉瓦仁波切的近侍Kuchar Thubtän Kunpel势力都很大。当时,政府官员无论高低都必须求得Kuchar Kunpel的支持,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要请求他的认可。但是,就像律经里所说的那样:
无论何时,任何情形,
水果都会退化、散落和腐烂。
那两人之间发生的事件让他们本人、亲戚和亲人无法承受,还有事件前后几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世道轮回突然发生波动,由吉祥向不祥、从青春向老年变化。这大大增加了我厌患和出离的想法。
那一年我每天都去布达拉宫作舍利圆满仪式,每周都换新的供品。供品从火化台上撤掉,从舍利塔的位置划定的时候起,随着工程建设一步步完成,我们开始把加持品放进去。
说到放供品,Desi Sangye Gyatso的时代出版了许多用作供品的密续很有名,我们使用了其中称为“布达拉宫后门外密封版密续”的,它们包括出自5世嘉瓦仁波切的《Illuminating Sun Clearing Mistakes in Filling Mantras》当中、分别放置在上中下层的5大心咒,男女夜叉的护法轮,还有取自Changkya讲经的《水晶镜》。所有东西都按照这两个来源作了准备。
另外,我们按照5世嘉瓦仁波切所撰《金主干庄严世界论》的目录说明,把金财神、白财神、多闻天王、Vasudhara、土地神还有5佛家等宝瓶(Five Buddha Families)放进山基的下一层(subbase mountain foundation);在对面的金色法座里,中间和四面放着盒装六臂大黑天、法王、吉祥天母 Magzorma、男女夜叉和5家Gyälpo King Spirit Guardians。每个盒里安放着各个护法的外依处、内依处和秘密依处如生命頗梨、生命轮还有身语意依处。另外,thread constructions、实体和密续、誓愿和心咒都按照相关本尊说明经法文字的说明作了充分合格的安排。
我们在塔的尖端如太阳和月亮部分,放置了象征寂静、增加及调伏的缘悲经护轮、僧伽召唤轮、大白伞佛盖母护轮、《洹河流水》(用Kurukula的神圣仪轨召唤三界的直言)、荣华萨迦族十三金佛法当中的三大女主神之一等。
另外,按照Dagpo Tashi Namgyäl所撰佛法教材《悉地之源》(Source of Siddhis)的说明,还安放了大法力自然轮、大法力召唤三界轮和达成一切意愿轮。《如愿树》(Wish Fulfilling Tree)是一篇珍宝经文,说明如何通过红色大甘奈施(Great Red Ganesh、第二组大法力神)秘心轮达到四业圆满。按照其所做说明,放置了秘心轮。
大法力神当中的第二位、增长和调伏轮(每只轮子都有三跺,当中有天、地与虚空)。还有上下及上下之间的九重堆叠轮,如男女轮和太阳月亮point-striking 轮(如愤怒尊Kagchöl Sumbaraja仪轨《光明耀眼珍宝》当中所说的那样)。
威怒尊Kagchöl Sumbaraja (第三类大法力神)成就法,底座上绘制了所有这些的图像,还有涂绘这些图像的颜料等,绘制这些图像所用的时间还有所有这些制作完成过程当中都严格按照先后次序进行,有关次序遵照的是相关本尊的经论还有5世嘉瓦仁波切的著述(如 《Touching and Seeing the Bouquet of Red Utpala That Unravels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Three Red Ones红色靑莲》)以及解说法轮的《钩召三界》[此书可见于《金色广大树干赐予功德与善业(The Great Golden Trunk That Grants Virtue And Goodness)》,它非常详尽地说明如何召唤和请求本尊留下。
撮政Ratreng仁波切、大臣Silön Yabzhi Langdun Kunga Wangchug、舍利塔官Kalön Trimön还有嘉瓦仁波切的四位僧官随从,与我们一同聚集到嘉瓦仁波切在布达拉宫的僧房甘丹寺 Yangtse,把那些祝福的密续卷起来放在塔里,并且为塔的建成办了法事。
政府送来的50只大箱子装满了圣物。我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无法描述的神异珍宝,附着了印度与西藏各派传承上师的圣物,如舍利、布匹、发辫、遗骨和其他圣物。我们每样各选取一些放在塔中相应的层里。当时在珍宝塔中忙碌的人们也获赐福德,圣物也有一些赠送给了他们。
我把自己获赠的圣物当作最珍惜的瑰宝,并把它们与其他从无比可靠的来源获得的圣物[我后来到西藏中部和后藏的一些地方(比如下文提到的Lhoka等地)朝圣时在当地的寺院里获赐了那些圣物]放在一起。那一年是藏历2600年。
1959年是土猪年,我在逃脱在西藏受到的压迫来到印度时,随身带着这些圣物,有些就放在这间屋里。但大多数我都进献给了14世嘉瓦仁波切了。随同的还有一个内容清单,好让这块功德田得以保存,以利众生。
由于反复涂盐,圣体基本干化,肌肉紧贴在骨骼上。这时,只见后背下方从第13根脊椎骨开始,显现一尊世自在像,头、手臂、腿和莲花座垫一共有大约6英寸高,整个佛像往外突出。这更加放大了我们的敬畏与忠诚。
我35岁时是土猪年。那一年3月除了宝瓶之外,金色舍利塔的上层和下层都装满了圣物。我们举行了仪式,用大白伞佛盖母和《缘悲经》把每面金色和铜色吉祥宝幢插在其各自相应的位置。我们还举行了仪式,把经过加福的吉祥天母, Chamsing等的底座放入中心部位。我们还把密续放在镀金佛塔的尖部当中,在Saga Dawa月月亮渐圆的吉祥时刻,把三件法袍还有报身服包括五佛家宝顶等放在珍宝舍利塔上。我们在做这一切并把舍利身放在座垫上的时候,那些政府官员举行了繁复而吉祥的仪式。然后,由撮政Ratreng仁波切带领全体僧伽会众,通过Shri Varjabhairava,举办了广大的加持仪式。
后来,政府在布达拉宫的“Sizhi Puntsog”大会堂举行了一场宴会,庆祝 “Geleg Döjo”(许愿功德)金色舍利塔建成。舍利塔官Zhabpä Trimönpa、工程官Ngolä、工匠们和所有照看圣舍利的人都得到了礼物。我得到一套衣物,包括下半身穿的zän sham袍、上身穿的tö gag¬袍、法袍chö gö、nam jar袍、羽毛缝制的僧帽tse zha、鞋子,还有一盒精美的茶叶和其他东西比如银子、丝绸和布匹。从最初侍奉圣体舍利塔到在金色“Geleg Döjo”塔里供奉密续直到给舍利塔以及圣物举行法事,总共进行了1年半时间。我对那些繁重的事务不以为意,觉得是自己有至高无上的福缘才得以作这种淨妙法事。
夏季闭关时我到了甘丹寺。应甘丹江孜寺 Para 康村的要求,在甘丹江孜寺的云堂向甘丹江孜寺和甘丹萨济寺的广大僧伽作了密集金剛Akshobyavajra灌顶,其中包括额外的一天准备时间。我又去了Para 康村 一周,作了一次密集金剛修习讲解。因为我不能亲自去当地一座很小的乡城 寺,我的代表Pawo Butsa and Gelong Tänpa Namgyäl回去了。
Dong扎仓送了一些通用资金帐上的钱来支付费用,在拉萨的一些乡城人也追加了一些供给,我就有了足够的东西可以给乡城桑培林寺,好让工匠们缝制一块精美的锦缎拼一块唐卡,它有三层楼高,主要描绘的是上师瑜伽法–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功德田,还有两位前任甘丹寺赤巴法王和业行王Trinlä Gyälpo。
火鼠年我36岁。2月初,67岁、身材瘦削的Gän 仁波切Lozang Tsultrim觉得有点不舒服,于是去看Shelkar医生Jigme-la。医生给他开了药,法会也做了几场,侍从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2月15黄昏,他还是圆寂了。我们感到很难过,但却无计可施。
大家只好振作起来,我亲手给他的遗体作了沐浴等。从我7岁长着一副小身板时起,直到这时,主要是由于他的仁慈,不知疲倦地给予我佛法教诲,才使得这头倔驴成长为人。并且,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在我的前任和后来的管事相续去世这样的时刻,他都独自承担管理拉章的义务、教导我关于俗务之事,他对于我在世俗和佛修方面的仁惠功德真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由于我一直与Gän仁波切密切来往,我很难正确地依止上师。尽管我做到了从不让他失望,但依止上师非常重要而且法力强大,由此哪怕是做出对上师极其微小的善行与恶行,都会分别造成无限广大的善果与恶报;我在他的遗体前忏悔自己犯下的一切过错。尔后,我们把他的圣体运到Chuzang闭关处。我在那里与上密院的僧人们一起举行了火化仪式。我在上密院和下密院举行的荟供法会和三大佛学院向长老们(比如三大法轮即西藏三大佛寺Lhasa、Samye、及 Tradrug–Falcon-Dragon寺的长老们)做了布施,尽我所能地为他的圆寂加以供养。
无上尊者Gän 仁波切于第15个甲子的铁马年出生于Domä Nangzang Kongjar 家,后来进入甘丹萨济寺完成了5大经论的修习,成为一名无比渊博的上师。铁狗年在拉萨的大法会上,他参加了格西拉让巴会考,获得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Känpo Pukang Lozang Kyenrab担任甘丹萨济寺住持要求退休。Känpo Nyagre Lodrö Chöpel在担任住持前的5年内,13世嘉瓦仁波切一直在考虑是否“委任赤江仁波切的老师Lozang Tsultrim”为住持。
可当他可能会担任住持的时期临近的时候,他却向Deyang Tsänzhab仁波切等人提出请求,说由于大家不断为这个职位竞争,而他又不懂政治,因此请求免于担任住持一职。可假如是别人,大家或许会高兴地接受13世嘉瓦仁波切的委任,把它当作自己最大的愿望。但Gän仁波切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点都不开心,当时这事让他无比焦虑,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夜不能寐。他的上半身患了体能失调症,双眼常常充满泪水,因此只好让乡城 Nyitso Geshe Trinlä进行照顾等。
每天清晨,Gän仁波切便起床进行修习,功课的内容包括上师荟供、6段上师瑜伽法、大威德金刚仪轨、药师佛和各种祈祷等。于是,他不教课或者研习佛经的时候就会坚持诵读《缘悲经》、弥勒心咒或观音心咒,从来不进行毫无意义的闲聊谈天。
他在甘丹寺的时候,许多江孜寺及萨济寺学院的学僧每天都来听他讲课,他也从来不知疲倦、从不气馁地讲经说法。他培养的众多杰出学僧当时已经在教导自己的学生,而那些学生当时已经成了格西;他就是这样留下了许多佛法遗珍。
这里说一下Gän仁波切是如何授课的。他虽然不会没完没了地进行阐述,但会用三言两语、微言宏旨地对一些难点和要点进行概括。比如我十二三岁修习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既兴趣不高,也无法听懂,于是Gän仁波切不会用很长的经文(比如宗喀巴大师的《Essence of Eloquence of the Provisional and Definitive》),而是用很短并且适合我理解程度的课文来教授我三宝和菩提心等内容,并且每次都教我推理的方法,让我对课文的意思有深刻的印象。就像发射出的一块石头能够追击一百只鸟儿一样,他的教学方法让我能够自始至终都能理解课文并且掌握其总体结构。
他圆寂两年多以后,我们才找到他的转世灵童。由于他没有杜固的称号什么的,我亲自照顾他并最终让他与众僧伽一起修习。我想通过供养他来报答他的恩慈,我回向给他1千万密续Yudrönma(称Pänpo Sengey Gangi喇嘛闭关)。帕绷喀金刚持开创了一个先例:我们在请求他为转世灵童占相时他写了下面的答复:
满月之时他应邀到达
白光之路的顶端,
白光发自弥陀菩萨之心。
如今他在兜率净土闭关,
由Aparajita相随。
这封“种子书”虽然没有注明日期,但由于其中说明上师圆寂是在满月之时,他出生于兜率天,因此此信不仅确定了要寻找他的灵童,而且还激发并且增益了对他的信仰。
3月,我去甘丹寺作供奉以纪念Gän Dampa圆寂,应甘丹萨济寺 Lhopa Geshe Ngawang Tashi的邀请,在甘丹萨济寺的会堂向僧伽(包括甘丹萨济寺和甘丹江孜寺的住持、喇嘛和杜固们)作了鲁依巴大师派62尊胜乐金刚灌顶。
那年的夏课期间,甘丹萨济寺扎仓的一个工作组开始工作,在会堂四周的圆形会见区安排了繁复的供奉仪式。我供奉了四周是珍宝花鬘和半花鬘、中间为35尊说非菩萨的百纳精致锦缎唐卡,还有带金甲衣护法像的半花鬘门帘。
我还在Dokang 康村会堂的12根短柱之间供奉了新会众旗,由百纳锦缎制成并且带头部装饰和12只香袋。做完这一切,我去了甘丹寺,在甘丹寺Ngamchö, 宗喀巴大师的周年纪念日,我向萨济寺扎仓和每个康村作了施舍供奉,并且安排了长年供奉。同样,在甘丹江孜寺扎仓我作了施舍供奉,还供奉了50盎司银子,作为常年供奉的资金。
我37岁时是火牛年。为了Gän仁波切的淸淨法事和我自己安度37岁的业障年,在大法会上作了恭敬施舍供奉以累积功德。在上密院扎仓,我除了为Gän仁波切作供奉外,还在每年的2月满月之时用50盎司银子作长年供奉。
按照我妹妹Yangtzom Tsering(她当时住在Lhalu Gatsäl家)的意愿,我向Lhalu护法庙供奉了Lhamo Magzor Gyälmo的内外和密座、吉祥天母身语意、功德和事业以及她的tendö经,还举行了7天的仪式来安放那些底座并完成经文(thread construction)的建造。它结合了吉祥天母经集当中教授的清闭关习法和5世嘉瓦仁波切和Tukän仁波切等所著的适格经论说法。
我在Chuzang闭关处的会堂聆听了Kyabchog金刚持讲授的各类至上密续精要(其针对的是那些具有惠根的人,这些教诫能使人在此生达到金刚持次第)、师利密集金刚圆满次第修习法、极简短《五道灯》著述等。
他讲解幻体(illusory body)时安排了非常广大的供养品、朵玛和荟供。金刚持喇嘛生起为曼陀罗主神,我们作了内供、外供、秘供等供奉,并且祈祷他根据大密续的传统讲解幻体。他作那些清静幻体供奉时,我还写了下面这首歌作为供奉:
喇嘛德钦宁波,一切上师与菩萨的化身,
传授诸密续之巅的师利密集金剛,
他悦耳的讲解流畅无碍,回荡着佛法;
就连梵天王和天帝释也无缘享此幸运!
虽然报身曼陀罗的福祉无法言说,
这支快乐之歌发自五内!
我将其进献给无与伦比的上师,
啊,帮助我吧,金刚兄弟姐妹,用清静的三昧耶!
虽然我的智慧低下,辛苦不足,凭着上师Akshobyavajra赐福的法力,
我快乐地舞蹈,为我们的万福!
我们能够穿越无上祕奥捷径的关口!
无边净土曼陀罗轮当中,广大密续
起伏升降,大风能量散布三界,
收入中脉无二径中,无上快乐!
清辉与二十四影像界同味,
直角三角形天成的微笑青春,
无穷无尽地释放到五色光形成的幻云,
舞者充满众曼陀罗、弥漫虚空。
虽然看似一堆迹象,却自有智慧性,
无碍智慧色现,一体女神,一味似多味,
愿我等历荣华色究竟天净土!
人说幸赖Indrabhodhi上师的仁慈,
无数众生得以解脱,无促迫与艰难,
我看人称“Odianna”者必定如此!
凭借坚固铁甲般的忍耐以解脱众生母,
示现含有母音与子音之密续义,
清净极端双幻的一切尘染,
愿我等歌唱Ali空间极乐之歌!
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无与伦比的上师听了这首歌表示快乐。不过,由于我一生都在hubbub当中度过,因此没有福份像自己所愿的那样亲自修习。这个结果无疑与其缘起一样,而这种缘起来自我前世诸生积攒下的深重恶业。
秋季歇息期间,我和Lhabu带着几个随从离开拉萨先后去了Yarlam甘丹寺, Mäldro Katsäl, Gyäteng, Chäka寺, Pangsa, Rinchen Ling寺和Rutog寺。我们穿过Täkar关到达Ölka Tzingchi和Samling。接着,我们穿越Gyäl Long关口,到达Chökor Gyäl、Lhamö Lhatso、Gyäl Lhatog、Daglha Gampo大佛殿和Zanglung闭关处。返回的路上,我们经过Ölka Chuzang、Chölung、Gyasog、Lhading和Nyima Ling,在Ölka下面的tzong温泉呆了几天。虽然Daglha Gampo的(Gampopa Dapo Lhaje)身语意像无比精妙,但因为体积不大,因此稍许有些不足。我还去了Gampo拜见Gampo仁波切,想请教他几个关于真正大手印和6瑜伽教义的问题。可能是他比较腼腆的缘故,我只得到他一点好听的简短回答。
我们穿过Kartag关,先后到了Zangri Karmar、Dänsa Tel和Ön Ngari扎仓。尔后我们又穿过Nyangpo的Tsang Chu河到达Tsetang。 我们又从那里去了Ngachö扎仓, 甘丹寺Chökor、Namgyäl庙、Nedong Tse组、Bäntsang寺、Tradrug Tsuglakang、 Riwo Chöling、Yambu Lagang、Yarlung的几个佛殿、Lharu Mänpay Gyälpo、Tagchän Bumpa、Tashi Chöde、Rechungpa的山洞、Tangpoche、Songtsän Gampo王的陵墓、Chänyä寺的几个佛殿、药师佛Rinchen Dawa、药师佛Tönpa Tsänleg Yongdrag在山上的几个佛殿、Chong Gyä Riwo Dechen、Göntang Bumo Che、Tsäntang Yü Lhakang、Sheldrag闭关洞穴及Jasa庙。
我到Sheldrag的时候向莲花生大士进献荟供。只见莲花生大士越来越辉煌耀眼,就像他的本体一样。我还看见他的双眼好象在动。他好象要说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我此后一整天都感到非同寻常,有一种广大而无法言表的祥福感觉。我意识到这是Ogyän第二大佛的赐福。
在我们所到的上述大多数寺院,我会满足所有讲经说法的要求,由此结下许多法缘。因而在那些Kemä地呆了几天。我还应Riwo Chöling僧伽的邀请作了密集金刚阿门佛大灌顶。
返回的路程经过Tsangpo河河谷,需要坐船过去。在与难以尽言、荣华天成Samye寺长者们进行长谈之后,我先后经过上下Chimpu和Yamalung,沿途向刚才说的那些长者们作了千供、百供、荟供等,还给那些僧伽做了法事,基本上都尽我所能地积攒了相应的功德。至于那些圣者的特征、经历和法传与传记和那些地方的圣物,Kyäntse的史经当中都有解说,在此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经过Gökar关回到了拉萨那石头丛生的地界。那年的冬课期间,我去甘丹寺供奉了4面精美的手缝大旗,上面还有铸金和铜制成的头,还供奉了产自中国的新式锦缎,上面有龙的图案,边缘还镶有老虎,用来半点会堂里的4根长柱。
土虎年我38岁。人神护法帕绷喀金刚持在人们的多次请求下,终于同意在甘丹寺山胜乐地结合4套注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著述。为了去甘丹寺,我早早就起来做准备,收拾东西以提出请求等。寺院下方奔流的河水边是草地,上面支起了一顶顶帐篷,还做了其他准备好迎接他。他和随从到达时,我向他进献了哈达和3尊觉悟身语意形,并一整天都充当他的侍从。
次日清晨,他来到甘丹寺,我们和甘丹萨济寺的住持及官喇嘛及杜固们(比如宋仁波切罗桑津珠)手里奉持佛香,护送他从主会堂入口附近走向预先在Dokang康村会堂准备的讲经法座。甘丹萨济寺的住持和扎仓的住持、众喇嘛和官员们一排排坐在那里,侍者依次送上茶水、米饭、油炸食品、水果等。我和扎仓奉上哈达和三3尊身语意形。仪式结束,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僧寮,在去他的僧房之前,他应我们的请求,仁慈地在我和我随侍还有那些康村上师的房间里舞动香烟。
我一连几天都从自己的僧寮向帕绷喀金刚持和他的随从发出请求。接着,在讲经开始前,我向珍宝上师和他的随侍们进献了合适的营养品,那些都特别好,因为原料(黄油、面粉、糌粑、茶叶等)都质量上乘。那些东西我们都作了供奉,因此他们不需要从市场购买。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各种原料的质量还有蔬菜等,并且按照合适的大小一份份地送去。
5月3日按照星象观测来说是个吉利的日子,他应邀去萨济寺Tösam Norbuling 扎仓的大云堂。现场有人演奏双簧管并且燃香以迎接他。接着,我们把这位一切菩萨的化身、三界众生的珍宝上师请上无畏佛法宝座,他端坐正中,安放莲足。
他那微笑的面庞看上去充满深意,他、萨济寺和江孜寺的住持和前任住持、喇嘛们、杜固们和官员们还有人数众多的僧伽(包括著名的护法如色拉杰寺Dragri Chogtrul 仁波切, 色拉美寺Kongpo Shartrul 仁波切 、新建的Chabdo Tsän-nyi 扎仓色拉杰寺Tsawa首任上师格西Jampa Tayä等),还有来自色拉寺, 哲蚌寺和拉萨地区的众位喇嘛、格西和离家的行者们,总共有2千多名听众过来,聆听他讲解那蕴含一切戒律精要的佛法体系、两位开路先锋龙树和无着、幸运众生获得解脱、蕴含四大的不二法门(该法门由于具有三大特征而尤其尊貴)、照亮三界的明灯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他运用4套大注极其精妙地解说了那些佛法。他以Pänchen Lozang Yeshe 讲说的Lamrim Nyurlam作为基础,讲解修习有关内容的体验,他在开始的时候用自己一亲身的经历讲解通往修习之路真是非常仁慈之举。
第一天,为了结下福缘,珍宝上师从头到尾检查了我们记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情况,共检查了3次,后来我又背诵了1次。那天我向僧伽散发了供奉。从那天起,就像漫长的第一天一样,他每天都讲两次,从午后开始一直讲到傍晚。后来,夏课要开始了,他只好每天增加一课,但一点也没有丝毫疲倦的样子。他的一生一直处于快乐之中。他天性仁爱,不知气馁。
讲经的时候,除非有施主负责散发供品给会众,我会每天向会众供奉茶水。虽然讲说的主要部分还没讲完,6月14日是一切皈依的化身、无上法王之王金刚持的61岁生日。为了不断享有吉祥、让他化身的三秘不变金刚性继续不断地伴随我们,我们举行了广大的荟供和5千供奉。13日,我们准备了菩提心法荟供品。
14日清晨,他按照寂天传承仁慈地同时给我们许下和接纳菩提誓愿。我们按照上师荟供和荟供的精深道供奉了空行母长生仪式。我给会众做了繁复的法事,毫无贪念地散发了供品。接着,在给金刚持喇嘛尊者进献了象征他殊胜诸像的头道供奉(我在供奉时进献了自己写的赞颂文,开头是赞颂他法身的殊胜功德和他天赋5大圆满功德)之后,供奉了广大的曼陀罗著述以请求上师与我们同在,直到万有的尽头。听到上师非常高兴地赞扬我对曼陀罗含义所作的解说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后来,甚至形成了在这类场合使用我所撰写在解说文的传统。
从那天之后直到19日,他不断讲该论的其余部分,最后一天还供奉了曼陀罗、三个底座还有象征性的供品。我也向全体会众供奉了法事。喇嘛仁波切最后总结了顺利完成的说论,在听讲的会众面前引用了佛主在话语:“我已经给你们指出了解脱之路,需要你们自己去实现!”他还说明为什么光听讲经说法是不够的,必须与观想和禅思密切结合才行。否则,如果继续把修习引向身外,那么就只会寻找别人的缺点,就会像一尊神沦落到鬼的地位,习法者会有被魔鬼带走的危险!他还引用了《中道之心》中的话:
“啊,蜜露一般的话语,比檀香尊贵!
众生心中如火的妄念,让他们遭受
的无比折磨,得到平息!”
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详细而丰富地馈赠至尊宝贵的精要蜜露。不仅如此,金刚持喇嘛还预言我和Gomang Kangsar仁波切将是他学僧当中最为宝贵的、如果我们俩获得长生,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觉悟的业行。Dagpo喇嘛仁波切说:
“子会超越父,孙会超越子,重孙超越孙!”
他还说由于这必然会出现,大家必须祈祷我们长生。在那里见到我在前文提到的喇嘛和杜固们如Dragri仁波切还有一些无疑能够弘扬佛法的称职格西们,并且受到如此之高的赞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为了放松几天,我们去Wangkur Ri休假。我做了烟供,大家围着甘丹寺Lingkor绕佛。在这当儿,我不断回想起他令人愉悦的话语:“嗯,这次,能够有机会在宗喀巴大师的寺院(monastic seat)传授广布其教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精髓,我们是如此幸运!”。他讲经说法的秘奥我一直珍藏在心里,当作滋润心田的蜜露!我从甘丹寺动身的那天早上,金刚持喇嘛让我戴上平常他自己戴的班智达帽。他不仅把金刚忤、铃和一卷《菩提道次第广论》(前3页写的是金字)放到我手上,还赠送我一只胜瓶和一只装满诸宝的银质事业瓶、一尊度母像、金刚持喇嘛的一只装满绿松石、珊瑚和宝石的旧杯子、一匹完整无缺的白色锦缎(上有金色八吉祥图案)。他还给我提了一些修行方面的建议,包括必须广为持守、修行和传播文殊护法宗喀巴讲授的经卷和仪轨。他坦诚的话语给了我无比的安慰。我的功德得到了无比的提升。
当时我的想法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沉陷泥沼,心思总是很散乱,而且没有丝毫修行经验,天生没有什么证果,修治也没有什么证悟,要侍奉佛法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由于上师具無上菩提心,我又与他有善缘,金刚持喇嘛圆寂后,就像一个比喻里说的那样,公鸡不在驴子当家,由于没有修行的根基以解说这位上师的说法,我只好在许多场合讲经说法的时候,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说过的经文、主要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后来,金刚持大喇嘛接受Dechen Sang-Ngag Kar寺的邀请前去的时候,我还步行去陪护。我们到Dechen寺的时候,正赶上举行祭祀齋宴和圣火舞表演。我也观赏了齋宴表演。我看那是极大欢喜,源于解说《菩提道次第广论》而慢慢累积起来的功德成熟的果报(讲经说法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功德圆满,没有丝毫差池或恶兆)。
从Tzöpa Rigtzin圆寂直到这时候,我和Lhabu都在按照“单宝身” 观想的习俗,自己负责管理僧寥。就在这个时候Dokang 康村Muli Lozang Döndrup接过了执事职位。
东嘎寺拉章的檀越多次请求我去充实并加持托摩格西仁波切昂旺格桑的舍利塔(他上一年圆寂)。于是,这一年10月,我、Lhabu和厨子Puntsog还有其他一些僧人(其中包括Kuzhab Kälzang Wang-gyäl)离开了拉萨,先后经过Gampala、Päld、Nakartse、Ralung、Gyältse、Pagri和其他地方,最后到达Drotö东嘎寺。我对着舍利塔念了心咒等,但推迟了加持仪式,直到新一年的庆祝会。
同时,由于我们已经过漫长的跋涉到了东嘎,我们觉得如果继续前行去尼泊尔和印度朝圣会非常吉祥。我们沿途经过Jaleb 关、Rongling 等地方,骑着驴子和马前行,一直到达Kabug ,在Tharpa Chöling寺的Dromo拉章呆了几天。接着,由一名翻译陪同,我们去了菩提迦耶、灵鹫山、那烂陀、拘尸那罗、舍卫城 、瓦拉纳西及兰比尼。在尼泊尔,我们向所有的圣所如三座大佛塔朝晋。有一天我去拜谒Namo Buddha,我们租了一辆公共汽车,驶上关口到达佛塔,但沿着关口另一侧下去的时候汽车马达抛锚,车子不能走往前了。大家只好继续徒步向前,直到夜里11点才步履维艰地到达佛塔旁边的小旅馆。当地有一些长者,我们克服疲劳,尽力给他们做了荟供和其他供养。
到菩提迦耶的时候,我们遇到Ladhaki的一位喇嘛,名叫Ngawang Samtän。他住在菩提中心客站。由于决定让他在菩提迦耶买一块地建一座新西藏佛寺,于是他请我在那里举行诵经仪式。当时大佛塔周围的土地都归Dzvaki国王所有,于是我们悄悄到达现场,在将要建造Pelgyä Ling藏传佛寺的空地上、在这一年11月满月初升之时,我手拿怖畏金刚密续,向田地护法和土地诸神作法,请求准予使用该土地、领有了土地并且作了护法仪式、赐福仪式等。我还作法,埋下了一只小宝瓶。
由于必须向菩提迦耶的大菩提荟供奉黄金以得到Dzvaki国王的批准等、从而向其致敬,我们去了他的寓所,礼节性地向他供奉了一些礼品。他让我坐在一张豹皮上---只见豹子的爪子和头都完好无损---向我进献了哈达,接受了我的舒手加持。他对我有好感,便借给我一头象去Silwatsäl朝圣,还借马匹给我的随从们骑。因为我从来没有骑过象,因此起初感到很新奇和开心,但在象背上颠簸得厉害,让我头晕目眩,受了不少苦楚。
到达菩提树下的时候,只见有不少西藏人朝圣至此,我与他们简短地结了法缘,向他们口授了Kabsumpa,宗喀巴大师赞颂佛主诵辞、他作的《缘起颂》(Praise of Dependent Arising)、三大祈愿文和其他经诵。
当时印度受英国人控制,当今的经济进步当时都没有。因此我们下火车后,只好步行或者坐马车到达各个朝圣地点。朝圣之后我们在返回途中到达Kabug,在那里应公共福利会的请求,在Tharpa Chöling前面的田野上给1千多名僧俗人等做了大慈悲大加行。
我们还到加尔各答和Darjeeling进行了短期旅行,以体验这两个地方的吉祥气息。在去Darjeeling的途中经过Goom古寺,应Gadän Chöling的请求,我在那里结了简短的法缘。
我39岁的时候是土兔年。藏历新年的时候,我被派到Kashang Tashi Chöling寺,应施主们的请求在大年初一写了一篇propitiat Kashang Guardian Näsung Gyälpo 的祷文。从Kabug经由Rongling, Tzaleg 等地的时候,我们到了东嘎寺,连续三天,对那里的舍利塔举行了多次的灌顶。
接着,应该寺众喇嘛和僧人以及老施主们(如Bönpo Kunga Ling-gang家的Pajo Dönyö)的要求,我在寺里的会堂给200多名僧俗人等讲解了15天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捷径》,最后做了菩提法会、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甘达巴五尊胜乐金刚还有大慈悲灌顶、若干护法如大黑天和法王随许灌顶,金刚瑜伽母辛都拉赐福,还讲解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以及上师荟供。讲解了一系列佛法,最终延长到3个半月。
我离开Dromo,与Pangda家的“生意大师”Tsongpön Tsechö住在他们在Pagri的家的佛龛房里。这期间我走访了一些寺院,比如Dragtog Gang(由上密院扎仓管理)、Richung Poto寺(由甘丹萨济寺管理)和Tashi Chöling的上下院。每座寺院都去一天,结下短暂的法缘。在Pangday Rakor我给一大群会众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Pälmo派)。
接着,为了健康,我去了Pagri Kambu温泉。这次准备和安排都由Tsongpön Tsechö进行。Tashi Lhundrub Ngagzur Ta Lama仁波切到了那里,我去迎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在Kambu“杏树”院(由修密者Damchö Yarpel尊者创建)。寺中藏有大量的经卷,我看了看一部分、好几卷的经书,其中有一卷的书页被打乱了,里面有一些手写的预言,虽然我的记性存在不足,但还是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
法力强大的观世音将有“圣尊牟尼佛”之名。
他的一切事业会像罗侯罗的那样。
闪电将击中他的大臣“噶哇史密斯”(‘Garwa–‘The Smith’)……
还有:
“他的一切事业会在鸡年完成……”
我查看这个预言是不是准确,发现对前任嘉瓦仁波切的评价非常华美,把罪过归咎于Demo仁波切。它预言,水鼠年中国军队会发生内乱。我还看到一个明确无误的预言,说嘉瓦仁波切会于鸟年去世;至于其他人,这里就不便提及了。
然后我就离开了,打算经过Pagri去拜访后藏的一些长者。我先后拜访了“扎仓Do”,一座Rva Dharma Senge创建的尼姑庵、Dotra寺和Chilung等,于5月满月之时穿过Drongdu关到达富丽堂皇的Sakya寺。在那座萨迦派寺庙周围的村中,就像Tzamling Chisang 的日子一样,给拉萨供奉的全世界护法神进献香烟供,要根据萨迦派的传承通过居处召唤当地的一些本尊,但其中的一些本尊已经入了自己的居处,正在一排排的人群当中发挥醉酒的效力。我住在一位萨迦族政府官员家,他的一位下级Majawa进了香、点燃了大麦糌粑和燕麦。
客房里有几位僧人在读一些放在那里的手书经文,并且就逻辑学、波罗蜜多和中观等等进行辩论和根据经文进行应答。僧人进行的讨论和内容广泛的祈祷方式与三大佛寺对辩论和祈祷的解说是一样的,只是几个地方的表述和长度稍有不同,比如美学等。我可以感觉到萨迦佛学院的辩证式教学法的修习体系和观想方法传入宗喀巴大师上师和他的学僧创立的格鲁学派。
那间办公室里经常举行很多修习活动,我们只好在河边的野地里扎帐篷。
这时Puntsog Podrang的Dagchen仁波切确实是萨迦族法座的官方代表。我只好去那里共进茶会、去他的寓所,恭敬地给他鞠躬,请教他关于萨迦派金法和Three Red Ones的修习问题,他只是说了句:“和那两个儿教师说吧”,就没再给我作更详细的解说。他给了我许多加持过的蜜露丸。
在我探访该寺上方和下方的圣址同时,他打发我去找世袭上师做老师,我专门会见了一些长老,如Jamyang Garzigma、Chödung Karpo Gyangdrag和Gorum寺的Sebag Nagpo Purshe,因此听到关于那些世袭上师教诫的种种描述。和我谈话的那些长老都很收悉他们讲经说法的情况,但好像不太收悉萨迦派密传比如诸金法。
我从萨迦派寺院出发,继续朝拜Marlam Samling的天护法寺还有荣华四面大黑天圣处Kau Dragzong,然后穿过Atro关,进入查荣(Charong)地界,接着去了Lhunpo Tse寺、Tropu Jamchen和Gangchen Chöpel寺,最后到达荣华Nartang寺,在那里看到许多圣物,有一座庙里有印度菩提迦耶圣地的完整模型,用檀香木做成,据说是在菩萨觉悟时做的。模型完整无缺,十分精致。我可以看得出,它就像菩提迦耶的Ghandola塔和菩提树一样,并且更加肯定印度菩提迦耶的圣地确实是菩萨觉悟之地。
虽然我很想继续朝圣,去Jangchen闭关处和Shvalu,但时间不允许,只好以后再说了。
我到达后藏北部的扎什伦布寺,拉章政府的一名官员给了我举行zur烟供的全套用具,十分华美。我住在一座新建的僧房,名叫Pände Kang,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在Yongzin Lochen仁波切的拉章里。
帕绷喀金刚持心怀大慈悲,使得众生的诸根清净。当时,扎什伦布寺拉章特别邀请他向聚在Dechen Podrang的几千僧伽传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幸好有上师 无与伦比的恩慈,我才得以获得佛缘、用我的头顶他擦去他莲足上的灰尘;再次如同父子般重逢,聆听他悦耳的谆谆教诲。
由于名闻遐迩的Kunzig Pänchen仁波切 还没有从Gyasog回来,他的僧寮空着,但我还是按照古老的传统去觐见并且行大礼拜,受茶供,并且进献了哈达、3尊身语意符底座和其他供奉。我在Kunzig仁波切尊者位于Kadam Podrang、名为“Podrang Gyältsän Tönpo”的上寮中的法座前,用了茶水、米饭和油炸食品。我离开的时候,他赠我非常好看的物品,包括一些甘露丸、手工制作的泥像、香、足够做一件zän袍的羊毛拼块。
床后面有一间密封的护法室,卧室内还有一卷佛经,现在也可以看到,据说是甘丹寺的化身经。他的转世住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从Pänchen Lozang Chögyän时起),因为那里是对传授佛法做出巨大贡献者的寓所。那里早已变得无比吉祥。我极其虔诚和欢乐地念诵了七支供养祈祷。
那里还供有历任班禅喇嘛的舍利塔、一尊很大的米勒佛像和许多大庙。我全部走访了一遍,在扎什伦布寺的主会堂做了供奉,散发供品等,积攒了功德。我们同Kyabying Tzasag和其他主要官员一起打开拉章送来装加持底座的箱子,里面还装满了各种非常吉祥之物。他们非常仁慈地赐我福缘,让我看那些。有一天,我于喇嘛金刚持在Dechen Podrang说法的时候,把那3个觉悟底座供奉给他,并且恭敬地做了法事和向那些听讲的人散发了供品。为了得到吉祥,我那天还听了一堂他说的佛法,从而再次泽被佛缘,品尝他法语甘露和感受他包容一切的恩慈。
我在扎什伦布寺的时候,每天都聆听法事讲经说法,因此许多最有成就的僧人来我僧寮要求我就各种他们关心的修习方法(如上师荟供和上师瑜伽法等)传授经文、著述等。授法一节接着一节。前任Lochen Chogtrul仁波切年纪尚轻的转世也在听讲。他请我给他作三大传承之主杰宗喀巴的随许灌顶,我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离开扎什伦布寺,去往Panam的Gadong寺,还会见了Gyältse Pögang部。两座佛寺都有许多圣物,包括一条耶绕巴大师禅定时用的喜金刚坛城唐卡、Kache Pänchen的衣物、印度佛经等等,我都瞻仰了一遍。
我应Karka Kashö定居处的邀请,去那里给当地的人做了长生灌顶。到Gyältse,当地人放了一张金色的床让我坐。我与Pälkor Dharma界长老举行了非正式会见,在Zhinä扎仓做了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简本著述。
我在沿途经过的Ralung寺、Pökya闭关处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寺院,都散发供品,积聚善气。我们经过Karo Pass、Nakar Tse等地时,乘船渡过后藏河(Tsang River),在Nyetang呆了一天,看见那尊会说话的度母像(那是度母庙里主要的圣物)和阿底峡尊者用来禅修的“不离”塔(‘No Separation’ Stupa )。当年6月我终于返回拉萨。
秋天,帕绷喀金刚持来色拉寺密续学院解说《事师五十颂》、做了密集金刚阿门佛大灌顶,还在色拉杰寺Hardong 康村作了金刚手菩萨大法轮(Vajrapani Great Wheel)大灌顶。我还受获了灌顶,从而获得浩如烟海般的赐福和蜜露。
雪域护法、手持白莲手印的降伏众生圣者化身14世嘉瓦仁波切宗座尊者应Domä的邀请,于8月末无上仁慈地莅临拉萨的Gangtö Dögu田野。政府事先支好一顶大帐迎接他。我与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的众喇嘛和杜固一起去迎接他。看见他相好的坛城,我如同啜饮解脱的蜜露。
铁龙年我40岁,在罗布林卡宫的泉水旁,十分感激地受获百家主Yongzin Tagdrag 金刚持所作的许多灌顶和随许灌顶,如五尊无垢顶(Tsugtor Drime)南無摩訶般若波罗密咒(Ushnishavimala)、五尊Özer Drime无垢光和Machig Drubpay Gyälmo派多安无量寿佛、多畏怒佛还有Rächungpa从印度带回的九尊白佛灌顶等。我还受获了Kyabchog Lingtrul 金刚持解说《成就大海》(Ocean of Siddhis)的密集金刚生起次第。
夏季闭关期间我去了甘丹寺。应甘丹江孜寺Para杜固的邀请,我在Para康村会堂里向500多名僧伽包括甘丹萨济寺和江孜寺的住持和喇嘛作了上师荟供和大手印体验解说。
当年冬天,我的本师帕绷喀金刚持派侍从Namdag-lag专门到拉萨,告诉我说已经确定要他解说直达麻利度母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从次日开讲。他说,因为我以后很难听到这样的讲授,我这次最好来、必须听讲。我甚至可以呆在那所闭关拉章,于是我马上动身去Tashi Chöling。
我在听这些说法的时候,受获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教诫。本师讲解时所依据的绿度母仪轨本经采自塔普金刚持的观想和仁波切自己对于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著述;还受获了绿度母业行的解说Letsog Charbeb,最后还受获了嘉钦雄登教诫的方法、成就与业行的口传教诫。
然后,(他说)为了吉祥,他口传并且广泛教诫了长生方法,就是结合白胜乐金刚瑜伽的修习念诵能-风金刚。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我心乱不平,沉迷于在拉萨做法事而难以自拔。仁波切知道这个,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可能永远丧失良机,再也不能受获如此精深的教诫。泽被上师(Father Guru’s)的巨大恩慈须弥山重达千钧,仿佛千万须弥山压在身上!
从上一年开始,Kyabchog金刚持 就不断在睡梦中梦见许多让人心乱的凶兆出现。他一直表达要去某个遥远的地方的意愿,仿佛因为受到困扰而不安。我们当中的一些喇嘛和杜固包括林仁波切金刚持、Demo仁波切、Dragri仁波切和Kongpo Shartrul为是否需要立即举行平静心神、保护上师的仪式进行了讨论。
我们请求进行长寿法会,于是所有听过上师讲经说法的喇嘛、杜固和格西都聚集在Tashi Chöling云堂。还有那些在独修的比丘,也都参加了更高阶的长生荟供,通过长生白胜乐金刚修习法打断空行母的邀请。我们反复请求他留下,直到有的尽头,身语意无有变易,达到不坏金刚,燃烧耀眼的至福,成为延续菩萨终生不灭教法、特别是宗喀巴大师教法的护法。
他回答:“我的许多学僧此次在此聚会,举行长生法会,打断空行母的邀请,无疑已经驱散一切业障!”执金刚神露出那样的面容,还说已经足够,看起来好像他只是为了平息我们的担忧才说的权宜的话。
铁蛇年我41岁。上一年摄政Ratreng仁波切突然辞职,Yongzin Tagdrag金刚持摄政。因此,新年第一天他的宏大坐床仪式在辉煌的布达拉宫辉煌举行。为了做准备工作,拉章私人办公室一大早就召我去拉萨普贤寺,举行室内吉祥长生仪式。我解说了团城,供奉了吉祥符和七宝,还念诵了吉祥就坐等谛文。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那一年在拉萨大发法会上帕绷喀金刚持举行了公开散供,并给会众举行散供。由于我也正在举行公开散供,有一天在举行公开散供的时候我们同时到达嘉瓦仁波切面前。在大会堂里,僧众根据杜固位次列队站好。本来我是要在金刚持喇嘛前头的,但我往后缩,跑到他后头。金刚持喇嘛说:“虽然可以有例外,但您必须留下!”于是我只好在他前头,但感到十分惶恐不安。
法会最后是荟供。想起那件事,我就观想另外有一个胜乐金刚的像站在喇嘛身边、而喇嘛则在亲自惠泽众生,接受第十天的荟供,但这样却使我召唤智慧尊很困难,于是我就观想那位上师是一切皈依处的化身,他的脉络和大种有英雄和空行母性、正在化身具足金刚体曼陀罗接受供奉。我觉得这样举行供奉非常有意义,于是在第一个月的25日单独邀请无上皈依体Kyabchog金刚持和他的随从们到我的僧寮,给他们供奉了一桌宴席好种下功德。
他心情愉悦惬意,讲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每一个音都像蜜露流自圣法,滋润我干渴的心田;就像一桌盛宴,一百种不同的风味,都是至高无上的殊胜意旨。他说的其中一样,是如果现任嘉瓦仁波切的健康如果没有障碍,就必然会变得像7世嘉瓦仁波切Lama Kälzang Gyatso,到时候我必须侍奉他,侍奉的时候要特别仁爱。后来,我担任嘉瓦仁波切的Tsänzhab(辩论搭档),逐渐获得Yongzin(导师)的称号。在我看来,好像帕绷喀金刚持多年以前就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我会受到很高的佛法恭敬。
有好多年Yangzom Tsering 一直请求帕绷喀金刚持为Lhalung Gatsäl 僧房的护法庙建外底座、内底座和秘密底座还有经文(thread construction)。金刚持喇嘛让我根据他的教诫为底座和经文(thread construction)的建造做必要的准备。于是,我把以前一点点积攒起来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今年大法会的荟供(Prayer Festival Great Ganachakra)一结束,他便来到Lhalu Gatsäl,在八名Tashi Chöling僧人的协助下,做着各种底座和经文(thread construction)的建造工作。我参加了当时的各种仪式。财务主任Lhalu Tsipön、Gyurme Tsewang Dorje、我妹妹和我当时还同时接受了长生囑累随许灌顶。
金刚持喇嘛从Lhalu来Dagpo Shedrup Ling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顺便造访Chagsam 10日修习会。我在讲经开始的前一晚赶回,供奉了带花朵和精致珍珠环的南迦锦缎袍、曼陀罗、那三个底座还有一条哈达,主要是为了请求他长生、做佛法和所有众生和我本人的护法,也是为了感谢他编辑了嘉钦雄登全套仪式行经,包括经文(thread construction)建造依止、完成和禳除法、朵玛禳除法、火供和增祿禄法。
他说:“我不大可能完成这一编辑工作。要相信以你自己记得的内容,以你的记录为基础……。”他就完成其余内容的编辑向我提出细节方面的建议,然后对我说:“好啦,把我给你讲的做基础,以同样的方法适当地补充其余的做法,就能编辑一部上乘的全套仪式行经!实际上我要求你做是因为我做所有这一切护法工作时,你都在场。”我把喇嘛仁波切的话当成命令,因为他自己事业广大,没有空闲时间做这件事。我后来后悔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他的话其实表明了他最后的业行(进入涅磐)。这与以前的情形相似:菩萨说了三次:“如果如来们愿意,可以历经一个又一个劫!”当时阿难陀中了魔罗,没有明白菩萨说的什么意思,没有请菩萨延长自己的寿命。
打那以后,有一天Norling Shözim Chung-gag发来一道紧急召唤,要赤江杜固和色拉美寺 Gyälrong格西Kyenrab Gyatso去上达兰萨拉。我去了以后,到了信息办公室,摄政Regent Kyabgön Sikyong仁波切告诉说我赤江杜固,已被提升为Yongzin(老师)以接替Zhabdegpa Tsänzhab Ling仁波切。由于需要临时增加一名Tsänzhab,而且如果色拉美寺 MäGyälrong Geshe Kyenrab Gyatso被任命为Tsänzhab,那么赤江杜固的位置将在林仁波切所排成道路的首位,而Kyenrab Gyatso格西则获得从前出现过的Tsänzhab称号。 于是,我遵照命令,在一个星相吉祥的时候,去参加一个与西藏政府僧俗的见面会确认此事。
4月15日,我与Kyenrab Gyatso格西一同去了罗布宁卡宫前室。我们第一次以宗座新任Tsänzhab的身份与宗座共进早茶。宗座按照传统方式供奉了三第座、哈达,礼节性的少许米饭和钱。接着,我奉命于用早茶的人们坐在一起。那天我受获了在家檀越等人的祝福,并做了吉祥供奉。
而后,与宗座共进了几次早茶,并参加了其他一些仪式。然后,我像布达拉宫的常务官一样,在摄政Yongzin Tagdrag 仁波切 处理政务而金刚持 Yongzin(老师) 林仁波切没空的情况下,按照吩咐聆听宗座阅读和背诵经文。因此,按照摄政仁波切的命令,我前去接受三座和哈达供奉,并向宗座做了扎西德勒初始敬礼。
从那时起直到决定任命两位老师,我都处于身份不确定度状态。这时,我的僧寮也挪到罗布宁卡宫一座Tsänzhab房里。那些侍从们小心翼翼,仿佛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宗座刚开始见到我时还有些腼腆。我遵照摄政仁波切的建议,一开始也显出一副保守的样子,不苟言笑。由于他年纪小,背诵经文的技巧不成熟,我只要稍微对他哥哥Losang Samten皱皱眉头,仿佛责怪他耍了什么把戏,就够了; 我从来都不需要对年轻的嘉瓦仁波切说出严厉的话来。
所有曼陀罗和家庭的不二之主、光荣殊胜的帕绷喀金刚持从他在Lhalu Gatsäl的僧寮来到Marlam Chushul 的Chagsam10日修习会,后来又去了Jangchub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后来,在6月1日,我听到的消息仿佛让我耳朵扎了刺:他已安住于广大无边、安详清净的法界,而我也与仁慈的上师尊隔开。体验了这种苦痛不幸的时刻,前世的业果降临到我头上。我心中备受痛苦煎熬,祈祷他的离去,尽量多做供奉,比如在拉萨Trulpay Lhakang所做的供奉。
他的管事Trinle Dargyä说我必须到来,以便向我询问关于珍贵舍利子的准备功夫及主持火葬仪式的事宜。于是,我到Tashi Chöling去。闭关处和拉章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忧心失望的人,全然失去了青春的光彩。这位金刚持喇嘛的僧寮空无一人,寂静无声,让我不禁落下泪来,一边哭泣,一边在庙中的金身——达波喇嘛仁波切——前占卜,得到一个面粉团,这表明他的佛体需要火花。我详细吩咐Tashi Chöling 的住寺僧Lozang Chöpel如何侍奉珍宝舍利体,将其送往Dagpo。
Kyabgön摄政命令Zhöl Kagyur印刷厂刻制Tuken Chökyi Nyima、贡塘 Tänpay Drönme、Je Sherab Gyatso选集凸印版和西藏中部罕有的其他经文的凸印版。他指定我和色拉寺美Tzänzhab主管该项目,我们为此效力了好几年。
荟供法会游行所用的两块镶饰唐卡已经破旧。政府要加以替换,于是下令由我监督测量众神的形制大小、将工人们升格为神,以及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检查尺寸。于是,我自始至终都从事监督工作,吹毛求疵地进行检查并作出纠正,从而避免了错误的产生。
这些年来,声称是我的近亲、姨娘、姐妹、子侄、叔公等的人慢慢多起来。就连曾经恨我母亲和她女儿的Ane Yangtzom 也对我恭敬起来,并对我母亲很亲切,等等。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
没有叔叔,也有了叔叔!
物质财富,我对你顶礼膜拜!
就像一个这样的事例:有一个人(讥讽地)对他的一只装了银子的袋子鞠躬(因为这只袋子吸引来许多新“朋友”和“亲戚”)。就像文殊沙迦班智达护法说过:
你富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
你破落的时候,所有人都成了仇人。
曾经长期在珠宝岛上聚集,
湖水一旦干涸,人都走光!
同样的情形,随着我命运的浮沉,有些人时冷时热,与我交朋友或者弃我而去。
水马年我42岁。1月12日,摄政Tagdrag仁波切下令众住持和上师在拉萨垂朗经堂聚会,向年轻的嘉瓦仁波切授予中戒和沙弥戒。我担任Drogdenpa即佐助,帮助僧伽受戒。
荟供法会一结束,按照下密院扎仓的一个内部传统习惯,新受在家和具足别解脱戒的僧伽,要从通用资金账户中支取一定数额用于散供、投入本金并在传统的佛法庆典上资助灌顶与穿法活动。今年,在新入比丘的敦促下,我在拉萨下密院扎仓的Changlochen会堂,给上密院扎仓的僧伽和下密院的所有会众以及三大佛寺来的人共2000多人做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大灌顶,包括连续几天的预备仪式。
夏季闭关期间,摄政仁波切下令,查勘罗布宁卡宫和布达拉宫所存印度和西藏各派学者与成就者手抄本和印刷版经文索引,并且编撰新索引,以方便查找不断累积增多的大量经文集和散编经文。于是,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整理编撰详细索引,添加标题并对经文进行如下分类:完整的经文集;《中观论》(Madyamaka)、《波罗蜜多经》(Paramita)、《律经》(Vinaya)和《论藏》(Abhidharma)等散经;辩证法、《菩提道次第广论》和修心等内容;密续,如各种新旧翻译学派系列密续仪式和通史、文法、诗歌、医学和星相等。
8月,Kyabchog金刚持管事Trinle Dargye住进扎西确林本寺孤零零的寓所,负责为他的圣体建造新舍利塔。建成以后,我们在塔内念诵了心咒,最后由我任金刚师,与出家的比丘们一道,做了怖畏金刚广大灌顶,做了3天,没有用任何简便的方式,而是严格精确地按照规定做完一切。在灌顶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我给檀越们開示,想起上师的恩慈,便唱了一首证道歌,请求尊者转世快快回来,歌名叫《孩儿在原野游荡,唱着忧伤悠长之歌》(Long Sad Song Of The Child Wandering On The Plain)。
《时轮金刚本续》(Kalachakra Root Tantra)有一章叫“全面抓住上师公德”,是这样说的:
无论为逝者立下何种公德,
他们都留给近亲,
公德会成熟紧跟他们;
就像牛犊仅仅跟随母亲。
同样,弟子怀着信念忠诚;
牢记上师的忌日,
供奉祭品,
便能究竟圆满上师的圣意,
达到上师的一生公德善迹。
格西波托瓦曾经说过:
Drom为这位老人作葬礼19次!
希望在无数来生与他相会!
于是,我设立了一个基金,一边每年1月1日为扎西确林本寺的会众做供奉和散供,一边做上师荟供法会和胜乐金刚(Chakrasamvara)坛城自入仪式。这一年在法会结束时,应Kenchen Dönpälwa或叫Tashi Lingpa Kyenrab Wangchug的邀请,我在拉萨Meru扎仓云堂给大约3千名喇嘛、杜固和僧伽,广泛讲解了捷径(Nyurlam)和文殊教义(Jampel Shel-lung)还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其中包括菩提法会。
水羊年我43岁。3月份帕绷喀拉章管事Trinle Dhargyä坚决邀请,于是我在拉萨Meru扎仓云堂,给大约3500名僧俗人等,做了一个月的体验讲解,讲的是捷径和《菩提道次第广论》合并的内容,包括最后在须弥山石头庭院里讲解菩提法会。
接着,应Namgyäl 扎仓领诵Trimön Chötzä Thubten Desheg和仪式佐助Kälsang Wangyäl-lag的强烈要求,我在布达拉宫Namgyäl扎仓密续(Secret Mantra) Gatsäl云堂,给700名僧俗人等讲解了15天《Lamrim Delam–The Blissful Path》,最后做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怖畏金刚和大慈悲者大灌顶和大黑天、法王、吉祥天母、多闻天王、四面大黑天及江森(Chamsing)等的随许灌顶。
夏季闭关期间,我在罗布林卡宫举行了一位住寺喇嘛的身业仪式。结束后去了Kyishö Yab-pü Ratsag Hermitage,在那里住了3天。那里有一尊金刚瑜伽母像燃烧着璀璨的福光,那洛巴大师用她来辅助自己禅定。我在像前做了金刚瑜伽母坛城修习供奉和荟供,还向那里的僧伽做了布施,最后留下一笔资金,用于每月上弦月第10天做修习供奉。
我应檀越Kyenrab Lhamo比丘尼的邀请,给大约100名僧伽(包括当地的居民和其他人等)做了金刚瑜伽母四大辛都拉加持灌顶。当时我做了几个好梦,但现在记不得具体内容了。
关于这件事,我年轻时和后来,有时候会在梦里听本尊和喇嘛们,或以凡象显现的圣者向我说出预言,预言有长有短;或者梦见相貌没有什么怪异的生物,或者看见一卷卷写下来的预言。如果第二天我告诉了别人,自己立刻就把它忘了。如果不说出来,就不会忘记,就像“猪头宴”那个故事一样。好像是真实的,但除了偶尔出现一鳞半爪、吉光片羽之外,通常都会错误百出,回想不起来,好像是由于退化而记忆日渐蒙尘。
那年秋天,我向嘉瓦仁波切和摄政仁波切告假,带着一小队随从(包括随侍Lhabu、Päldän和 Gyumä Trehor Ngagram Tsultrim Dargyä)去西藏中部Penyul朝拜各个圣地。那里收到早期噶当派大师们的赐福,十分吉祥。我们经由到潘波(Penpo)的Go关到达廊塘(那是格西郎日塘巴的道场)、那烂陀(全知Rongtönpa的道场)、Patsab Lotsawa舍利塔、Nanam Dorje Wangchug修建的Gyäl(胜利)寺、一尊弥勒佛的化身、Tangsag的甘丹Chökor寺、格西夏惹瓦的舍利塔等。
由于Patsab Lotsawa翻译了长生经,带来了吉祥,如果绕行有名的Patsab舍利塔,就能驱除长生障,因此有许多人在那里绕塔。这位Lotsawa把月称尊者的《入中论》翻译成了藏语,使得应成派在西藏大为兴盛。为此我也绕起来,累积了为数不多的几次绕佛功德,想感悟那精深的佛理。
Zimo金刚持Jampa Kunga Tenzin Päl Zangpo是从前世帕绷喀金刚持那里,受获了萨迦派密续(Secret Mantra)嫡传修习,获得了该派教义的真传。他第一次去Nyangdren Chuzang 闭关处会见帕绷喀金刚持时,虽然Zimo仁波切知道“大黑天十七说”有随许灌顶、经传和口授,但仿佛年老昏聩,他却显得心存疑惑,把此事丢到一边,好像没有兴趣的样子。 Zimo仁波切要离开的头一天夜里,梦见一个很大的法座。上面有一堆老人的白发、唇上和脸上的胡须,那情景十分可怕,表明大黑天很恼怒,因为他不接受大黑天的教诫而不快。于是,他次日请求受获完整的灌顶、口传和教诫。这事我是听金刚持喇嘛亲口对我说的,还说了是如何渐渐传给他全部教诫。于是我对他笃信不移,可由于他始终呆在潘波(Penpo),我这次见到他是唯一的一次。
那次我去拜访拥有众多圣物的那烂陀寺Zimo拉章,非常幸运地见到了仁波切本人,请求他教授我深奥的佛法。他欣然同意,并且設宴款待我们。另外,我还应附近Chogyä拉章邀请,与Chogyä Trichen仁波切进行了非正式会见。
我还向Tangsag甘丹Chökor寺的僧伽口传了《善功德之本》,在那里还看到一部Drelpa Dönsel的经卷,是《密集金刚意义详细阐释》(The Clear Illumination Of The Meaning Commentary–of Guyhasamaja),是月称尊者曾经用过的圣物。
虽然甘丹Trichen Jampel Tsultrim(如今的Kamlung杜固的前任)和他的同父哥哥已经去世,但他的侍从们一再恳请,我于是去了Kamlung闭关处(Kamlungpa尊者的道场),住了3天,瞻仰了Kamlungpa的舍利塔。由于Kamlungpa有些早期上师们的僧寮和闭关处散落在各处的山洞,因此无法一一拜访。
应西藏中部Töger Lhading官宦家族的邀请,我经由Pända Jeri Tagtse到了Lhading的定居点。由于当天正好是当月的10日,我与Gongmo Lhading家族一起,举行了荟供,还做了金刚瑜伽母自灌,并应众位檀越的请求,唱了如下这首证道歌:
纯净的Keajra色究竟天
一个美丽的姑娘,是降世明王的优雅母亲,
示现无数化身,
是福士到达空行母净土的引路人。
在六十四“E空间”诸空行之城
微笑的Chandali无比美丽,
灵活戏耍,舞动如闪电,
玩耍亦如是,福气滋生。
中脉八片花瓣烘托着佛心,
脱离影像,净光福母,
五光闪烁的神奇女神,
长出无可思议和合之相!
多么欣悦,深邃奥秘的捷径!
如此福乐,聚集的洁净三摩耶!
荣光荟供福乐和合,
这种因缘超越聚散!
我住了几天,给一大群人,包括那个官宦人家、还有一些在闭关的僧人们,做了金刚瑜伽母加持,还给当地人做了观音随许灌顶和长生灌顶。
应Tangkya寺的邀请,我为那里的僧伽做了13尊怖畏金刚大灌顶。为了达成Marlam Pagmo Chöde僧伽的心愿,我离开Lhading,给他们的寺庙进行了开光等,然后经由Dromtö返回了拉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些圣地尽可能多地做了供奉,还在那些寺院做了布施。
木猴年我44岁。4月,我遵从Kunling Tatsag Hotogtu仁波切之命,在Kundeling的云堂为1千多名僧伽讲解了一个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夏天,应Taiji Shänkawa Gyurme Sönam Tobgyä的敦促,为了给他过世的儿子Dechen Gaway Wangchug种下功德之根,我在拉萨须弥云堂给3千多名僧众,做了5天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大灌顶(包括准备事宜)。
8月,我去Tölung泡温泉保健。由于正赶上下密院扎仓僧众在Lung的夏末泡春泉,我便应众主持、喇嘛和官员的邀请去了Yarlam Tantric Center,给僧伽们读传下密院关于密集金刚的3大殊胜经文(称为“亲手传递之教义传承”)中的2种:《密集金刚五次第Dolagyuma》和《Dolagyuma解说》,还向会众做了布施。我在那里做了2周的温泉浴疗。我遇到了来自Tölung Ragkor的一些人——我的前世就出生那里的一所房子里;我给大家发了些小礼品。
我在从Tölung返回的路上,Tsering Drölkar(她是Bayer家族的女居士,住在Mäntö寓所)兴之所至,向我发出邀请。于是我在拉萨Shide扎仓的云堂,给大月2700名僧伽(包括来自三大佛寺、上下密院和各个闭关处的众喇嘛、杜固、格西和学僧)做了大约一个月的体验教诫,讲的是菩提道次地Nyurlam和文殊语录(Jampäl Shälung)的合并文本,还做了菩提心法会。
我给当地的乡城扎仓寺供奉了4面很大的绗缝锦缎立柱会旗,以装点云堂里的4根大立柱。旗身是虎皮做成,上面有很大的龙形图案织物,旗头呈杯形(cheppu-shaped);还有一整套经藏,上面布满甘珠尔经文,准备送给Dongsum Rig-nga家。
学者们摆脱不了虚荣,说起名位时滔滔不绝,因此,这时证悟的河流难以向上达到荣耀的顶峰。因此,那年冬天我从拉萨Mäntsikang医学院邀请了一位大师、来自Tölung Yangpachen的Gelong Päldän Gyältsän到我的办公室(在布达拉宫上层的文化学校中),与甘丹萨济寺Tzemä杜固一起,受获他讲解带图示的作文和诗歌“指路”教诫,内容依照妙音天女的语法和Getse Pandita Gyurme Tsewang Chogdrub所撰语法著述《百道阳光》(Hundred-Fold Sunlight),还有本经“作文矿藏”(Pandita Rinchen Jungne Shiwa著)及其由Mindroling Lochen和Lama Lhagsam所做的注解。我当时打算完成那些实例,但由于其他一些因缘而搁置一边。
那年10月,潘波(是Kändrung Chöpel Thubten的堡垒)Lhundrub Tzong的居民与色拉杰寺扎仓来收贷款的人动手打架,因为双方就贷款应生多少谷子做利息的问题发生分歧;有些居民被打死。Kändrung向摄政领导的政府发出申诉,摄政派了6名秘书进行彻底调查。正要传唤肇事头目讯问时,赶上木鸟年的大法会,还有Tsemön Ling Hotogtu大会考,嘉瓦仁波切Gyälwang仁波切已经应邀去主持会考了。由于色拉杰寺和上下密院的众住持和官员以及会众都在场,为大法会和茶供等法事安排地方的事只好推迟3天。
政府高官们下令说明谁对谁错后,大法会可以正常开始了;可当法会和荟供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道判决:色拉杰寺和上下密院住持都遭到驱逐,一些官员和收息人被人从会众当中驱赶出去,放逐到很远的城堡。这造成色拉杰寺和上下密院许多僧伽谴责Kyabgön摄政仁波切等。这样一来,一两个人的恶行最后导致最大的恶业。
当时及还有后来的一次都让我感到无法承受(另一次是Ratreng仁波切贬抑一些僧官),因为只要开始进行仪式,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佛缘就会发生断裂。可无论我如何诚心诚意、毫无私心地向Tagdrag仁波切的管事Tänpa Tharchin提出防止发生矛盾的建议,都于事无补。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
你纵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阻止下雨,
也只能祈祷雨水倒流,一厢情愿!
木鸡年我45岁。因为哲蚌寺内的甘丹颇章年深日久,摇摇欲坠,最高政府下令进行大规模修葺。此次宫殿西侧最高处要拆除重建。嘉瓦仁波切寓所门附近有一间女神吉祥天母的神龛室长期被封,破损特别严重,有人去那里进献哈达的时候生了病,还出现过其他的不祥之兆。摄政仁波切下令让我举行一场仪式,把里面的圣物移走。
因此,在拉萨的荟供结束后,我带着Namgyäl扎仓的仪式僧如领诵师和上师等去了哲蚌寺,给吉祥天母做了几天供奉。移动神龛的头一天夜晚,我梦见一个巨大的云堂,里面的神像装得满满登登,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朵玛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我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走不过去。这时,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走了过来,面带笑容,给我指了一条穿行的路。我认为那表示女神对自己的神龛挪移感到高兴。
我们第二天移动神龛时,宫务大臣也代表嘉瓦仁波切到了现场。他打开护法神龛的门,起初别人无法靠近,也不能处理任何圣物。虽然我对禅修的见识和技能没有信心,但因为自己至少做过吉祥天母闭关,同时还念诵过心咒,而且前天夜晚的梦也给了我信心。于是我一边念诵本尊和女神的心咒,一边拿起几条哈达和象征性的东西,把它们送到阳光寓所(Sunlight Residence)。
然后,其他参与仪式的人:领诵师、高僧、建筑官Känchung、宫务大臣等人,都动手搬出无数圣物、像供(visual offerings)、武器和甲胄等,都是多年来慢慢聚集起来的。另外,女神真人大小的银质主像有一个底座,带一片血海、一只骡子和大火背景,共有1层楼高,还有两尊随从(有头)的塑像,约有8岁儿童大小。那些塑像原先制作的时候是单独做的,所以移动起来好像并不很难。我们把塑像、骡子和血海分开,送到东边的寓所,我同时让Namgyäl的僧们在仪式音乐伴随下念诵大量的迎请文。所有负责搬迁的人(包括我自己、宫殿翻新官Känchung Ngawang Zöpa和宫务大臣还有一些最热心的喇嘛、杜固和哲蚌寺四个扎仓的格西)安排了广泛的供奉和朵玛;神像请出来在寓所重装时,我们用那些举行了Kangso(圆满和悔除仪式)和荟供。
护法神龛室内有一个很大的盒子,里面装有各种唐卡。我们打开后,发现一幅古代的唐卡,表现的是热译师的禅定尊怖畏金刚。许多头堆积在一起,是按照热译师的空行口耳传承(Kadro Nyengyu )教诫绘制的。还看到5世嘉瓦仁波切让自己的密续佐助Trinlä Namgyäl临摹的一幅,因此那里各有一幅原件和临摹件;还有一幅唐卡表现的是Drogön Chögyäl Pagpa 的禅定尊(Gönpo Gur)帐篷大黑天。只见他在画面上双腿站得很直;还有许多唐卡表现了各种奇异的故事,比如有一幅画的是Rishi Vishnu,画师是Zurchen Chökyi Rangdröl。还有一幅唐卡描绘的也是帐篷大黑天、早期萨迦大上师的禅定尊,以及几幅Pälgön Zhäl (Glorious Face大黑天像)。
有一只朵玛盒里有一系列祈愿文和供奉文,由6世嘉瓦仁波切Tsangyang Gyatso所撰,另有两三份请求护法梵天(Lamo Tsangpa)预言各种俗事的文字,以及答复。另外还有一捆纸卷非常有趣而且奇异,比如有些是献给格萨尔(Gesar)、讲述对于生活方式礼仪的知识;手写的诗句书法相当不错,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宫殿翻新的同时,也在翻新Gepel闭关处Gyälway Podrang的凯旋宫。我去Gepel闭关处作开光仪式、建筑仪式和移动诸天及诸龙仪式。举行这些仪式的时候,我和其他工人都没有感到丝毫的惑障。我认为如果没有三宝和护法是无法完成这一切的。
后来,哲蚌寺宫彻底竣工之后,我带着进行仪式的Namgyäl扎仓僧人去,为吉祥天母主像和像座(就像以前在布达拉宫门槛护法神龛所作的那样)召唤吉祥天母示现,并连续7天做了各种感恩供奉和茶供。虽然前任护法室内好像没有thread-construction,但上面下令做一个新的。因此,我做了一个新的thread-construction,举行了内容光放的thread-construction仪式。
那年夏天应Tse Potala Namgyäl 扎仓的Kusho Tserab-lag请求,为了给他死去的母亲及檀越积累功德根,我在Jarag Lingkay的云堂,根据菩提道次地Nyurlam和Jampäl Shelung的合编本,给1千多名Namgyäl扎仓的全部僧众,讲解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当时Namgyäl扎仓的僧伽们刚完成夏季闭关,正在因边界放开而愉悦。结束的时候是菩提心法会,拉萨的Darpa护法神Jowo Chingkarwa加持通过神谕赞扬了我,对我讲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加以祝贺,还向Namgyäl扎仓決疑说,从今往后,他们每年都必须负责请这样的法课(如 《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畏怖金刚等的生起次第及圆满次第等),一个接一个讲,不得中断。
那年秋末,我应前文提到的Bayer家族女士Tsering Drölkar请求,在拉萨Zhide扎仓为2千多名僧伽(他们已经受获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畏怖金刚本尊大灌顶)——包括众喇嘛、杜固和色拉寺、哲蚌寺,以及上下密院的格西——广泛讲解了上市荟供和大手印。
那年冬天,Kyabgön摄政仁波切任命Gomang Gungru Gyatso Ling 杜固为另一位辩论搭档。他得到了Kände Cheka座位,而我则升任Darhän。我上面的职位是Tzasag、长官(Ta Lama)和Taiji等。根据先前的传统做法,我以新身份去觐见嘉瓦仁波切和摄政,所有仪式都吉祥如意,毫无差错。
我46岁时是火狗年。在拉萨举行大法会期间,在古老的须弥城堡里,对法王的护法涅仲进行了通灵召唤。护法神供奉了曼达拉、3个底座和哈达,面带愉快的表情说:“无与伦比的导师、净饭王之子的珍宝教诲已经大为沦落;大师啊,在这一时刻,您给我们以如此广大深邃的教谕,就像蜜露,滋润幸福的弟子,这是何等吉祥啊!”
按照传统,祈愿法会结束后,嘉瓦仁波切就要在哲蚌寺的Kungarawa辩论庭院花园中,开始修习辩证法和推理。可为了使准备仪式更加繁复,在他的Tse布达拉宫Yangtse寓所举行了吉祥开始仪式。宗座坐在中央,摄政王Tagdrag仁波切、Yongzin Ling仁波切和我、Gyatso Ling还有色拉美寺格西Kyenrab Gyatso等在左右坐成两列。我们一起念诵了Ka Nyam Ma(《齐天六庄严与二尊者颂》)经和《文殊诸名称》(Expression Of The Names Of Manjusri),因为Gyatso Ling和色拉美寺格西拉的声音差别很大,一个高一个很低, 显得十分刺耳,Yongzin Ling仁波切大笑起来。这让宗座也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大笑,念诵仪式几乎完全打断。这让摄政王仁波切皱起眉头,可虽然他发起怒来十分吓人,但人们还是无法忍住笑。于是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助理、管家、仪式佐助还有侍者,都开始发笑。大家禁不住大笑,这其实是个吉兆,表明宗座的修习会达到最上精深的境界。
从此以后,除了有事打断,比如我们参加政府的活动,否则我们3个Tsänzhab每天下午都会轮流与宗座对话题就各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如果我们自己有事,比如讲经等,可以告假。
至于无比仁慈唯一最高上师帕绷喀金刚持的转世灵童是谁,Nagshö Tagpu仁波切所见的幻像、Panglung嘉钦雄登的神谕和Gadong护法神的声明,还有我反复做的查验,都完全吻合,的确是找到了。 那位找到的小灵童在ütö Drigung出生。有人把他送到偏远的Tashi Chöling闭关处。 2月上弦月那天,他在自己前世的法座上坐床,我也特别到场,做了一系列供奉,第一道是大海净土(曼陀罗)布供。
3月上弦月那一天,应下密院新戒比丘团的要求, 我在下密院扎仓的云堂,给一大群僧伽,主要是上下密院的僧人,做了5天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大灌顶,还做了预备,并且对《事师五十颂》做了著述和传授。
摄政王Sikyong Tadrag金刚持下令,Tagdrag僧伽的普经和密续念诵活动(如三种基本戒律仪式)、特别是严格按照荣华下密院程序进行的广大Geleg Charbeb加持仪式、还有自生、前生(self-generation, front generation)、宝瓶和灌顶仪式,以及密会世自在火供法会等,都要重新修订。我完成了修订。同样,Dragkar Ngarampa拟定的《法王金刚剑压制死灵仪式》(Dharmaraja Vajra Arrow Si-Spirit Suppression Ritual)先前的手写本和下密院僧伽所用的修习小本之间有许多不一致。他们请求摄政王仁波切赐予新的版本。可由于他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做,他下令由我去做。于是,我依照怖畏金刚通行经文、特别是参照Dragkar Ngarampa所讲授佛法的章节内容,编撰了Dorje Rirab Tsegpay Trulkor(“示现堆积如山的金刚轮”),以供在压制死灵的念诵仪式上用。
初夏,应拉萨一位居民,居住在肉市下方的Män Lhamo Tsering的要求——他要为去世的一位受在家戒的行者Tsewang Norbu种下善根,我在Namgyäl扎仓的Jarag野地扎起的帐篷伞盖下,为3千多名会众做了25天《菩提道增广论急速道》(Lamrim Nyurlam–The Swift Path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教诫,还在结尾的时候,应Namgyäl扎仓的会众要求,给1千多名已经受获怖畏金刚大灌顶的人,做了15天深厚教诫,讲的是13尊怖畏金刚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瑜伽,还讲了立体三维曼陀罗。其间偶尔穿插讲解大朵玛仪式观想、法王朵玛和几种火供等内容,还毫无保留地解释了那些修习法的一切。
虽然Namgyäl扎仓肯定有绘画和沙画的优良传统,却没有口授传承如何建造立体曼陀罗。经过与Kuchar Chöpön、Känpo Lozang Samten及Lobpön Tänpa Dhargyä等人协商,我们开始口传和讲授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和怖畏金刚三维立体曼陀罗的建造方法。最先开始讲授的责任就落到下密院的Trehor Ngarampa Tsultrim Dargyä肩上。于是, Namgyäl 扎仓的大约8名僧人包括上师和领诵师一起在甘丹江孜寺及哲蚌寺完成了曼达拉的学习和制作新曼达拉。他们做得十分精美。
那一年6月,我的肠子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病了20天左右,接着又得了水肿一类的病,差一点丧命。西藏政府医学、天文学院的首席专家Känchen Kyenrab Norbu尊者(他仿佛药王再世)还有宗座的医生Känchung Thubten Lhundrub给我看病。此外,法事已经做完,而且他们给我治疗时毫不懈怠,我终于在当年9月痊愈,至少可以出门了。
那年冬天,我应Trehor Zhitse Gyapon家主仪式师Ngawang Dorje(他是色拉杰寺最好的袭师之一)和他弟弟Döndrub Namgyäl要求,开始在我在罗布林卡的办公室给大约50人评述《菩提道增广论急速道》(Lamrim Nyurlam)。可过了几天后,由于听讲的人当中有几个色拉杰寺的学僧,一天,主侍者Känchung Thubtän Legmön来到我的住处说,我在罗布林卡讲《菩提道增广论》仿佛是引贼入室,还说我歇息一段就好了。于是,我回到在拉萨的僧寮,给大约100名发愿者讲评了余下的部分。因为此事传到摄政王仁波切那里——虽然他没有表示关切——那么肯定是那位侍者自己胆小狭隘的怕事心理造成这一小插曲。
火猪年我47岁。前任摄政Ratreng仁波切和现任摄政Tagdrag仁波切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虽然二人都无可争议的是位大师,实现了很高的舍离和了悟,但为了针对学僧们各自的需要来降伏其心,诸佛和诸菩提薩埵运用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幻觉化身降伏他们而无论他们清净与否、就算是魔罗和罗剎也在在所不惜。 尽管真如唯一,但为了示现给平常的学僧,如文殊护法萨迦班智达所说:
坚持不懈要搞分裂的人
就连密友都会弄得分开;
巨石总是受到水的冲击,
难道不会碎裂?
就像他说的那样,Tagdrag仁波切一边有管事Tänpa Tharchin、管家Thubten Legmön,还有Kändrung Ngawang Namgyäl。而在Ratreng仁波切一边呢,有他的哥哥Tzasag、Zhide Nyungnä 杜固和色拉杰寺Kardo杜固、几名侍者。他们制造了分裂,通过各种机会,当中的许多机会先后歪曲了人们提出的申诉。因此,情况让人看起来这些高僧的心似乎不是相同的。
他们代表Ratreng仁波切所做的第一个仪式,在某些地方显得要伤害摄政Tagdrag仁波切的样子,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因此,摄政与Kashag在2月23日晚联合采取行动,并和Kalön Zurkangpa Wangchen Geleg、Lhalungpa Tsewang Dorje还有一支很大的由四角(Drazhi)军营的官兵组成的分队,把Gyälzur仁波切带到Ratreng面前。
这个情况直到次日中午时分才公布。 当时我正在拉萨自己的僧寮里。于是Kalön和Rampawa Thubten Kunkyen喇嘛给我送了一个秘密口信,说我最好立刻去布达拉宫。因为Kalön和喇嘛自己必须在布达拉宫住几天,他们认为我应当也准备住在那里,于是我立即动身前往。
当晚,Kashag下令把Ratreng拉章和Yabzhi Punkang封锁起来,并且传唤Ratreng Tzasag和Läzur及Punkang Kazur Gung Tashi Dorje父子到布达拉宫。这两位官员和他们的助手同时遭到流放并监禁在布达拉宫东边的大炮塔里。次日,Ratreng仁波切的同党(包括Kardo杜固、Zhide Nyungnä杜固和Trehor Sadu的房子遭到封闭和上锁,Kardo杜固和Sadu Gyurme也遭到监禁,关押在东边的大炮塔里。正要逮捕Nyungnä喇嘛的时候,他带着妻子秘密逃跑了,还带了一杆枪。
2月27日,Ratreng仁波切遭到软禁,经过Pelpogo La Pass色拉寺前面和Tsesum的原野,顺逆时针方向绕过布达拉宫,通过布达拉宫下方的东门进入东边的大塔楼,那里驻扎了重兵把守。为了在西藏大会上广大的会众面前询问他,召唤他从布达拉宫东边的台阶来回时都用重兵看守着他。我在布达拉宫的办公室看见过他。这位权威大喇嘛此前出行时威风凛凛,许多政府和私人侍从侍奉左右,如今每天必须经受会众的审判;四周除了士兵之外,一个侍从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让我十分不悦,可谁也无计可施。我在布达拉宫的办事处看见他。
3月17日晚,我们听说Ratreng仁波切已于狱中亡故。前一天,对Ratreng仁波切的上诉进行判决的会众没能达成一致,于是我思忖Ratreng仁波切身故时是否无牵无挂,因为我担心他会得到严重的判决。我想不到别的什么理由能让他如此突然地去世。后来,有许多谣传,说他是被监禁他的狱卒杀死的。 Ratreng仁波切的哥哥Tzasag和Kardo杜固杜固被链条锁住,监禁在罗布林卡卫兵兵营的内牢和外牢。所有聚会的的大小官员都一致对他施以重判,判他终身监禁。起初,Pungkang Kazur父子和Sadu Gyurme遭到监禁,因为怀疑他们曾与Ratreng仁波切过从甚密,后来消除了他们与那场黑暗魔法的牵连,于是将其释放,一如既往地过着舒适的生活。
当时色拉杰寺扎仓的官员们大多数都无权干预政策问题,许多扎仓的人(比如Tsenya杜固)在政府所在地聚集进行示威游行。现场十分混乱。下噶伦Chögyäl Nyima、Magchi Tzasag Kälzang Tsultrim、Kändrung Ngawang Namgyäl、Tsipön Ngapöpa Ngawang Jigme和Namlingpa Päljor Jigme到达四角兵营进行敦促,于是守军威胁说要把色拉寺夷为平地。色拉杰寺的僧众只好让步,于是这场争斗才没有迅速蔓延和严重扩散。
由于Ratreng寺拉章的侍者们杀死了四角兵营派去封锁拉章的17名士兵,政府派了大军在总司令Kälzang Tsultrim和北方司令Zhakaba Losäl Döndrub带领下来到Ratreng寺。他们对Ratreng寺monastic seat和寺庙进行了猛烈的炮击。Ratreng寺拉章的财富可以与财神(Tzambhala)的相媲美,都被士兵抢走。政府下令将该寺拉章夷为平地。
想到这种轮回苦乐起伏不定,无休无止又快如闪电,让我不禁想要奋力摆脱此生诸多空虚无常之事,立即遁入大山。像一只受伤的麋鹿,沉浸于三別住和四尊者教命的甘露。通过三别住的修炼,经由身语义的修习在此生实现圆满觉悟。可由于此生种种表象和爱执不断的困扰,我不能斩断那些让我自己惑乱、让他人失望的业行纽带,只好将此事暂时放置一边。
由于发生了刚才所说的情形,许多站在摄政仁波切和Ratreng仁波切一边的平民辱骂和排斥当中的一个喇嘛,可如果把这事看成是向学僧所作的示现和僧众所面对的强大业力,那么就不能肯定地说那些平民真的造了排斥那个上师。目犍连尊者、恰卡拉罗汉(Arhat Charka)、Tri Rälpachen皇帝等人在其一生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十分小心,不要把过错加到圣者的头上,也不要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让我再次引用“朋友聚会”当中的话:
即使自己没有过错,
如果依靠恶行之人,
自身也会遭到怀疑,
恶名声会传播很远。
依靠不合适的人,
会因此遭到责备。
正如前文所说,摄政王Kyabgön Sikyong Tagdrag金刚持是一位密续大师,是神圣曼陀罗大海当中的“转法轮者”。前任摄政王Ratreng 仁波切 也非同寻常:他年轻时时候曾住在Dagpo,有一次他把一根木桩插进一块大石头,还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留下他那些神迹的圣物都保存在Ratreng的主要佛龛中,任何人都可以亲眼看到。
然而,即使那些神迹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是圣者,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众生功德较浅,而且由于上文提到的Tagdrag仁波切和Ratreng仁波切的侍从、还有仿效他们的人们很坏——他们的心灵收到魔罗的迷惑,用胆敢败坏此生和将来诸世福德的恶行——那一大堆令人发指的恶行——对待无比强大的圣者、特别是对待那位上师和三宝。想到如此伟大的上师——他是一切众生之友——的殊胜行迹遭到凡人的误解、被他们的仆人玷污,我觉得甚至是亵渎了佛祖。佛祖想到洁净和恶浊世界众生的福祉,因此在许多经文中说到需要对娑婆世界进行净化。
那年夏天,应檀越Trehor Sadutsang家的邀请,我在Namgyäl 扎仓主云堂前面的Jarag Linga原野里,依据Kachen Yeshe Gyältsän撰写的本经和精彩注解,以及依据班禅喇嘛Lozang Chökyi Gyältsän的佛龛,给超过3千人开示了上师荟供。除此,也广泛地开示甘丹传承大手印。
接着,我受获了Kumbum Minyag仁波切开示和传授的《方便究竟实义宏论精要:阐明中庸之道意旨》(Essence Of Eloquence On The Provisional And Definitive, Illuminat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Middle Way;宗喀巴大师著);Kädrubje的《简论空:打开福者双眼》(Tongtun Kälzang Migje-Short Writing On Emptiness To Open The Eyes Of The Fortunate
);Gungtang的《开示佛法深意赞》(Commentary To The Praise Of The Meaningful);《修心阳光》(Mind-Training Rays Of The Sun);《修心八诵》和《利器之轮》。
那年秋天,嘉瓦仁波切按照传统,开始在佛寺研究佛法;还为了开始学习逻辑学和辩证法,去了哲蚌寺。当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我与随从一道前往,呆在Kungarawa佛法辩论庭中的一间办公室里。摄政王Sikyong仁波切也按照惯例从3大佛寺的7个扎仓当中选取了几位Tsänzhab:这次除了我们3个,还新增了洛色林Gyälrong格西 Lozang Döndän、Deyang格西Chöpel Gawa、色拉杰寺Hardong格西Ngödrub Chognye及甘丹江孜寺Serkong Tugsä Thubten Tobjor。
举行重大仪式当天,在Kungarawa佛法辩论庭院,三大教派所有在家和出家的政府官员和住持、喇嘛以及杜固们,在嘉瓦仁波切和摄政王Kyabje Yongzin Ling还有我们7位Tsänzhab念诵《六庄严与二尊者颂》(Ka Nyam Ma– Praise of the Six Ornaments and Two Supreme Ones))和《文殊诸名称》(Expression Of The Names Of Manjusri)直到“佛法(别解脱戒)胜利旗帜牢牢树立……”,摄政王都一直从《波罗蜜多经》的开头进行记忆的考试。
嘉瓦仁波切和新老Tsänzhab们一起念诵完,嘉瓦仁波切接受每一位Tsänzhab的考试。从我开始,我提出一点,我们从《波罗蜜多经》的开头进行辩论。最后我念诵了一些吉祥话语。接着,众人按照传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接下来,我在各个主云堂、4座扎仓、Namgyäl扎仓、Tashi Kangsar和Gepel闭关处等地伴随着各个盛大仪式的传统列队行进活动。哲蚌寺的各项盛大仪式结束,嘉瓦仁波切便去Marlam Nächung城堡,迎请化身法王多杰Dragden。我亲眼看见护法神悄悄地在嘉瓦仁波切面前露出皮面具底垫、骡子等东西。
然后,我伴随行进的队伍走到帕里(Pari)山边的色拉寺Tegchen Ling。我住在靠近色拉寺寺主云堂后面的Dänma 康村上层。嘉瓦仁波切去色拉寺寺主云堂、3座扎仓和Hardong 康村时我在他身边伴随。宗座去帕绷喀闭关处进行例行造访时,我去了Tashi Chöling闭关处,在那里看见Kyabchog金刚持Chogtrul仁波切,向他供奉了长生灌顶并口传了几部经文。于色拉寺的仪式结束、宗座回到布达拉宫后,我还去住在那里。
Sumdän大金刚持Gyälrong格西Lozang Samdrub仁波切说我必须去帮着给两层楼高的宗喀巴大师和他的两个心子的金身加持。金身是新造的,在拉萨下密院Drakang Changlochän云堂的金身群中。我与下密院扎仓的全体僧伽用密集金刚做了广大的Geleg Charbeb加持仪式, 包括准备、主题部分和结尾3个部分。仪式结束那天,把格西仁波切和重修官Taiji Shänkawa的名字写进檀越名录时,我做了祈愿,在心里示现了尽可能多的供奉,还供奉了吉祥八珍等。
晚秋的时候,宗座去了布达拉宫后,摄政王Kyabgön Sikyong仁波切下令,对布达拉宫生活区上层的图书馆藏历世嘉瓦仁波切所用的浩瀚经文,进行索引修订和详细记录,因为色拉美寺Tsawa Kangtsän Tritrul为前几世嘉瓦仁波切修订得不够彻底。他还下令由我负责,所有Tsänzhab格西协助。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座红色宫殿顶部北侧二层的图书馆大约有3千部经卷,我们在15名左右的Namgyäl僧人们协助下,把它们全部取出来,分门别类,再用布包起来。我们7位Tsänzhab格西在布达拉宫生活区3层楼的各层干了很多天,不遗余力、不辞辛劳地仔细查看现有的各种索引,把乱了的页面重新排序,并插入新的索引。
经文当中有《宝积经》Stacked Jewels Sutra,来源于密勒日巴出生的房子中;这是全知者布敦仁波切使用的,里头还有他亲手写的注;还有许多早期著名的称职学者和瑜伽师如Kädrub Norzang Gyatso、Shvalu Lochen、Chökyong Zangpo——护法神Bhadra等研究过的经卷等,并且许多都是他们亲手撰写和作注的。第5世嘉瓦仁波切撰写的经文集中有些他列为“Crazy Laughing Tantrika of Zahor”修持法。我作了查对,发现内容十分广泛。因此,许多经文是由5世尊者手写的,有些是由Desi Sangyä Gyatso作了注,等等。
总之,有些经文记录了佛陀的话;有些是前世各派各宗学者和上师为了开示佛陀言论的意义所写的无门户之见的著述、佛法和通史,以及各种关于传统知识内外领域的经文等。内容完全是复杂、令人难以想象。有许多珍本我从来没有见过,标题我没有听说过。但当时的任务十分艰巨,没有时间轻松地研究那些经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继续开始新的工作,布达拉宫东北的Gadän Nangsäl阳光生活区收藏了内容非常广泛的经文,我们开始做详细的索引。下图书馆有数目极其宏大的经卷。我们受命要在适当时候编制索引,但从来也没有再接触此事。
土鼠年我48岁。荟供大会结束后,3月望,应上密院住持的代表哲蚌洛色林寺 Minyag Kyorpön Lozang Yöntän的督促,我在拉萨Ramoche上密院辩经庭中,用了5天时间(包括预备日)给大约4千人(如上密院全体僧伽等),做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大灌顶,还应Tsedrung Lozang Gyältsän的请求,给去世的Kashag Edrung Trätse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为他种下福德根。就在这段时间,勇猛护法、无比仁慈的帕绷喀金刚持的转世Chogtrul仁波切第一次开始修习无与伦比的最高密续瑜伽(Tantric Yogas)。
东边Dagpo Shedrub Ling的僧伽前来给宗座供奉长生法会,庆祝宗座在各大佛寺修习佛法。此时,应Zhide 扎仓官员邀请,我在Zhide扎仓给大约500人、主要是Dagpo扎仓的僧伽做了大慈悲者大灌顶,接着在拉萨Tsemön Ling扎仓的云堂,为300多人向宗座去世的侍从Kenchen Tsedrung Lozang Kälzang的哥哥Käldän Tsering做金刚瑜伽母四大灌顶赐福(Vajrayogini Four Initiation Blessing),还做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教诫,总共8天。
那年政府完成了甘丹寺主云堂的翻修,为了协助摄政王Sikyong Tagdrag仁波切对其进行加持,我与Namgyäl的仪式僧们一同前去举行了广泛的加持仪式,共用了3天。摄政王太过疲劳,不能进行加持中的寂静与愤怒火供法会,而且因为仪式还没有完成,我便接着进行。为了加持主云堂的翻新,我供奉了茶、好喝的米汤,还做了散供。
摄政王先去了拉萨。因为负责工匠翻新云堂工程的官员Taiji Shänkawa Gyurme Sönam Tobgyäl坚决请求,我在主云堂辩经庭中给甘丹萨济寺和江孜寺的僧伽们还有工匠们做了宗喀巴大师长生灌顶。
每年夏季,在Dragyerpa佛法课程的后半段,上密院扎仓的僧伽的确会学习曼达拉的画法、主要是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而且要接受各位住持、喇嘛和领诵师的考试。可是,除了一些写下来的问题和答案,没有关于三维曼达拉开示传统的记述文字,也就没有实际做法供观摩和禅修示范,因此智力稍差的人难于根据文字加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通过与各位住持、喇嘛和官员商讨,发起了一场每年一次的常规训练,内容是修习立体曼达拉的修造,从当年开始,不再间断。
在此期间,我在罗布林卡宫(Norbulingka)和布达拉宫与嘉瓦仁波切一起从摄政王Sikyong Tagdrag金刚持那里,受获了5世嘉瓦仁波切的所有密观(secret visions)灌顶。
土牛年我49岁。那年春天,应下密院一些新出家僧人的请求,在拉萨下密院扎仓的云堂,我给一大群僧伽包括上下密院的众住持、喇嘛与僧人还有三大佛学院的喇嘛、杜固与僧人,做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大灌顶;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和怖畏金刚Ngagtu随许灌顶;大黑天、法王、拉姆(Lhamo)和多闻天王随许灌顶;还为大约1千个发愿每天念诵勇猛英雄怖畏金刚(Solitary Hero Yamantaka)仪轨的人,做了勇猛英雄怖畏金刚大灌顶。
我在49岁的“业障年”(obstacle-yea)为死者种福德根并清除恶运,在释迦圣月专门派我的随侍Päldän 带一队人去Ölka 国、Samyä寺、Traduk寺、不丹和南方的其他朝圣地进行供奉,积攒功德。在此期间,我向嘉瓦仁波切讲授了语法和发音符号。
5月,应拉萨Jeti Ling居民Sönam Rinchen家的邀请,为了卑谦的Lozang Drölma去世,我在Zhide云堂按照Rinjung Gyatsa仪轨当中所说的内容,给超过1千名会众、主要是三大佛寺的众喇嘛、杜固和僧伽,做了诸本尊的随许灌顶。
在罗布林卡宫(Norbulingka)进行夏季闭关期间,从6月25日起,我的老毛病肠病又犯了。我还患了严重的腹泻,但到了7月2日,因为所有人(在家和出家人)都必须参加在罗布林卡宫举行的Lhas夏季戏剧节开幕仪式,我泻了一个小时,这让我身体系统受到扰动,当晚腹部剧痛。因为腹泻异常严重,我感到浑身剧痛,不能走动,当场倒在床前。我体温突降,失去了知觉。
当时,我的随侍Päldän点燃了Agar Thirty-five lung–energy wind,还混各了糌粑的药香,然后用他的手掌捂热我的头和脸。当晚我勉强支撑了过去。第二天早上,西藏政府医药天象学院的长老上师Ku-ngo Kyenrab Norbu和年轻的住持Känchung Thubten Lhundrub赶来。他们对我作了检查,还为我把脉,发现我脉象微弱,于是两位医生轮流离开戏剧节来为我把脉。多亏了他们的精心治疗,还有为了清障所做广大法会加持的法力等,而且因为我的福运还要由信众供奉加以维持,尚未到头,我腹部的痛疼稍微有了缓解。到4号晚上,嘉瓦仁波切派了他的首侍Känpo Jampa Chözang和财务主管Palha Thubten Ödän带着宗座的palanquin给我用,他们还把我从罗布林卡宫送到我在拉萨的僧寮。 腹泻停止后,过了3个月我才恢复了精力和体力。
众人打算给当地的乡城寺建造几尊新佛像——一尊由金和铜制成,高约2层楼半的无量寿佛像;两尊比真人大的佛像(一尊白度母、一尊尊胜佛母)。原本想在康区建造主体,面部则在拉萨建造,以确保其特别好看。造好以后,我安排人给佛像装点珠宝并在里面放入心咒,然后将其送到康区。 乡城寺地区的人还按照我的指令,在扎仓的云堂右侧修建了几尊新的三身佛像和一座新的无量寿佛佛庙。
那年冬天,我在布达拉宫期间,嘉瓦仁波切说要找人为上密Dugri Nagpo法王修造新的内外和秘密基座宝物。因此,我对前任嘉瓦仁波切舍利布包裹的宝物进行了重新包装。在事先测定星象会特别动乱威怒的日子,由首席雕刻匠Päljor Gyälpo受获怖畏金刚灌顶,并且在修建过程中不断修习仪轨。他把底座布涂成白色以后,他把种自字放在各个感官及心间心咒圆环上,接着又把它们涂上颜料,因此底座的各个圣物做得都合乎规制。
有一把铁刀的语基(speech bases)带一块牌子,上面刻有心咒,还有男女阎魔心咒轮;还有一根棍子的意座(mind base),是檀香制成的,底部有一把锋利的普巴匕首(purba-dagger)。还有一个母刀(a base of the mother)的底座,是一把三刃刀,装饰有黑丝绸,上面写着心咒。另外,还有罗剎随从的底座,是32把铁刀,刀刃上泼了毒血;一个毗湿奴铜箭底座,插在未去势的红牛角做成的箭鞘里;还有一个形状为水牛的外座以及一个毛发很长的shaggy 牦牛底座,脖子上挂着杏木心咒牌子;黑漆涂成的内座,各种形状和心咒涂了血、仪轨、莲花甘露、ghiwam 和musk ;两只骷髅(一男一女两个阎魔)的秘座,脸部自然从背部伸出,像上都涂了漆,因此表情更加突出;那两只骷髅连接处内部,只见一位法王的身形画在一块尸布上;还有小牛等,装满了怖畏密咒物和陀罗尼密咒并封上印。 这些底座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底座完成后,便升为神并予以加持等。所有一切都合乎规范。所有这些底座(除了那些唐卡)放在盒中,我们把它们放在嘉瓦仁波切在布达拉宫的Narim寝殿中各自的位置。
我们集中这些东西的时候,夜里我房里有很大的“梆”和“咣”的声音,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新唐卡供奉给嘉瓦仁波切那天,他的首侍Känpo Kyenrab Tenzin突然中风;有一天,我从拉萨去自己卧室的路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从马上摔下来等,出现了各种烦扰的迹象。由于这位上秘法王是文殊宗喀巴教义的秘密及严格大护法,这些迹象表明护法们当时正在场。
然后,正当我做完这一切,便来了命令,要给Lhamo Magzorma 做新的底座。至于法身底座,还有一条“说话的”唐卡,是嘉瓦仁波切在Narim 寝殿禅修的支助,因此不必做新的。我给语座画了一只空行母Meche Barma(燃烧的火焰)镀金唐卡,给意座配了一面镜子,里面画了BHYO;给行座,配了一根檀香金刚棍子,装饰了写有心咒的黑绸和一个未婚女人儿子的头壳(里面装满密咒物)、各种血和药物。外座是一只由黑丝绸做的乌鸦,里面填充了谷物和药村,还有一个加持的Lhamo像画在人皮上。 内座是一个用黑丝绸做的私生子的头颅,里面的填充物当中是一个三叉戟的生命轴,用火化过的木头制成,喂有毒药和血,裹在尸布中,布上用血写着Lhamo的长生唤-轧-杀密咒,还有一个私生子的心,里面填充着风卷起、没有落下的树叶,一半树叶上写着Lhamo的心咒,它对面的另一半是Lhamo身形和注以及各种血、谷物和加长心咒。身体上还有黑绸,手里拿着得胜旗,头上插着一块孔雀羽毛。密座是私生子的心,它的形状是三根管道保存完好,里面是从Lhamo Lhatso 取来、人眼从未看到过的石子和很大的四边黑石,上面用莲花血写了BHYO。还有一枝箭是从长在黑色大石头中间的7根连在一起的野竹子做的,上面装饰着乌鸦的羽毛,写着BHYO 心咒,字母一个个上下垛起来,直到羽毛的位置,从羽毛底部,本尊心咒及Lhamo的杀密咒加上心咒,背后是一根在毒药和血里浸过、包着虎皮和豹皮的铁尖、交叉的尴尬毛、黑色丝绸密咒、镜子、贝壳、窗帘布等等。还有一些铁刀和匕首。有一次雕刻匠们用金子做了一轮太阳、用银子做了一轮月亮,用彩线做了个球、红色的骡子、黑色和白色的骰子等。 所有这一切都制作都符合嘉瓦仁波切Gedun Gyatso对Lhamo 三大事业、5世嘉瓦仁波切密封秘密观想(Sealed Secret Visions )Son文字的描述。做出底座后,加持等仪式都很好地做完了,那些都密封在黑漆盒子里,外面是怖畏设计图案,然后当着Lhamo的面把那些请到布达拉宫寝殿。
大约这个时候,我和宗座嘉瓦仁波切一起受获了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根据Läkyi Shöpa经文做的17尊大白伞佛盖母的大灌顶。
铁虎年我50岁。为了给去世的Tsamkung女尼Anni Puntsog种下福德根,应她的信徒请求,春天在拉萨Tsamkung庵先后给100多名誓愿者,做了五尊甘达巴(Gandhapa)胜乐金刚大灌顶,和甘达巴身曼达拉大灌顶(Gandhapa Body Mandala),还尝试开示了甘达巴身曼达拉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体验(Gandhapa Body Mandala genera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s)、四大金刚瑜伽母灌顶加持(Vajrayogini Four Initiation Blessing),并教诫了金刚瑜伽母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Vajrayogini genera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s)。
应色拉杰寺住持Trehor Thubten Samten的强烈要求,我在色拉寺的夏季闭关期间,在色拉杰寺Känyän扎仓的云堂,给色拉杰、色拉美和上下密院的多数僧伽,以及每天从拉萨和哲蚌寺赶来听讲的僧人——共有大约5千人,根据Delam、 Nyurlam、及Jampel Shälung三部经文合成的内容,进行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体验教诫、修心七要法(Seven Points Of Mind-Training)教诫、还有六支上师瑜伽法(Six-Session Guru Yoga)教诫,共讲授了1个多月。 我对精通广大经文、云集的觉悟上师们讲经,真如同批着豹子皮的叫驴!听讲的人当中,有哲蚌洛色林寺格西Yeshe Lodän,他是三大法座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有一天,我讲完《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来到我住处,说他很高兴我讲授悟道时没有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而是联系自己的亲身体验。 我没有哪怕是一点点修习经验作为支撑,只是当个传声筒,鹦鹉学舌地重复无与伦比的仁慈上师的话语,但他好像对讲授的这些佛法百听不厌,觉得回味无穷。
这一年初夏,位于拉萨城东南面与宝瓶山大致平行的空中,有一颗彗星挂了大概一个月,这是个不祥之兆。还有,我在色拉寺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期间,有天晚上天刚黑,我们突然听到好像万炮齐鸣的声音,从四角兵营的方向飞向色拉寺南边。不久,发生了异常强烈和持久的地震,色拉杰寺扎仓屋顶的金色gangeria装饰还有德胜旗上的铃铛没来由地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当时正住在札仓楼上的寓所,所以起初很害怕。可经过深思熟虑,就放心了,觉得业果决定了没有做坏事,就不会有坏运。当时,西藏到处是炮火隆隆,地震让哪里都摇摇欲坠。中国红军的气息似乎正在扑面而来,仿佛是个不祥之兆。
杜固Trehor Beri Getag仁波切去了一趟昌都,想要阻止中国共产党毁灭西藏,并且襟怀坦荡地去了汉人和藏人正在商讨的地方。Getag接受过摄政Sikyong Tagdrag仁波切教授的许多佛经和密续,还和我有长期的师徒关系,矢志不渝地对我保持信仰和忠诚。他总是舍己为人,尽其所能帮助别人,人们从来不会丝毫怀疑他有过错与恶行。 可是,就像我们人人都会遇到的障碍那样,我们自己的政府鬼使神差地怀疑Getag杜固,还把他囚禁了起来。最后他死在昌都,据传是被毒药或其他什么害死的。想到自己再也无法与他相见,我十分懊悔,可也无计可施。
9月8日,中国红军突然到达昌都。藏军难以抵抗,逐渐丧失阵地。后来,前藏首脑Kalön Ngapö Ngolä还有平时和战时总司令等,以及一大群人被红军从昌都的Drugu寺抓走、投进大牢。形势变得越来越恶劣,于是两位Kyabgön Chöyön 仪式大师、Kashag、及几名秘书一起去罗布林卡旋转日光殿召唤乃穷和Gadong护法Shingjachän 。Gadong护法全身匍匐在嘉瓦仁波切脚下说:“眼下该嘉瓦仁波切负责西藏政务了!”乃穷也作出同样的请求。
于是,Kashag、几名秘书和西藏政府立刻一致请求并授权嘉瓦仁波切宗座负起所有政务和教务事宜,嘉瓦仁波切同意了。10月7日,Kyabgön Sikyong Tagdrag仁波切放弃摄政地位。8日,在布达拉宫Sizhi Puntsog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摄政把象征政务和教务双重权威的金轮献给宗座,还举行了坐床仪式。当天,宗座大赦了西藏各地囚禁的所有犯人,包括Ratreng Tzasag、Kardo杜固、Tsenya杜固和Kalön Kashöpa。
后来,由于红军的进攻越来越猛烈,宗座于11月10日任命Kuchar Känche Lozang Tashi和Tsipön Dekarwa Tsewang Rabten为并列代理摄政。随后,嘉瓦仁波切宗座、Sizur Tagdrag 金刚持、Yongzin Ling仁波切、众位大臣、秘书、宗座的侍从和随员分成小队,悄悄经由罗布林卡离开布达拉宫,到达边境的Domo。我带着一小队随员,包括Lhabu、Päldän和Gyumä Ngag-ram Trehor Tsultrim Dargyä。我们要在那里的Nyetang度母庙瞻仰一些圣物,比如一尊会说话的度母像(阿底峡尊者用它进行禅定)还有金洲“不分身舍利塔”(Inseparability Stupa)。
第二天,我们正在经过下江乡(lower Jang ),三大法座当中举行冬闭关的僧伽听到风传说嘉瓦仁波切和他的随员们正在经过,于是沿途聚结了众多的僧伽。可宗座身着便装,于是他悄悄经过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和我到达的时候许多僧人围在我们周围,一边向我们扔哈达和钱币,一边落泪,握着我们的马缰绳不撒手,想要不让我们走,因此我们简直寸步难行。我们告诉他们不久会再见等,以减轻他们的焦虑。我们没有拾起僧人们像雨点一样撒到身上的钱,住在附近的村民们一定得到那里的一些“证得钱”(siddhi of money’)吧。
当晚我们住在曲水村(Chushul)一家村民家里,可因为三大法座的许多僧人向我们涌来,我们只好再次离开,去往会合的地点。下了Chagsam轮渡后,我们在Chuwo Ri闭关处遇见大上师Tongtang Gyälpo派的几位长老。接着,我们渐渐经过Gampa Pass、Yardrog、 Karola、Ralung、Gyältse及 Pagri 等地,最后到达下Domo。当时宗座在Chubi Domo大臣室,我的随员和我,还有嘉瓦仁波切的母亲、Tagtser仁波切还有嘉瓦仁波切的其他近侍住在Chubi扎仓的顶层,每人的卧室都已安排好。这一时期,出于对内外形势的考虑,宗座及其随员都暂时住在Domo,并且在那里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向其他国家寻求援助在当时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策略,我、Gyumä Trehor Chabril Tsultrim Dhargyä 和其他人呆在原地,而因为Päldän从未去过尼泊尔和印度朝圣,我便派他和商人Lozang格西一道去印度和尼泊尔。因为我让他携带了不少东西去那些圣地供奉,也借机做了广大的供奉。 我自己、Gyume Treho Chabril Tsultrim Dhargya和其他人呆在原地。
铁兔年我51岁。宗座嘉瓦仁波切、Yongzin Ling仁波切、我自己及Namgyäl 扎仓的侍从僧人们向吉祥天母供奉了周期朵玛,而当时在现场的所有政府人员如噶伦(大臣)们则在Domo的几间主室内举行了简单的新年仪式。然后,我去前任摄政Kyabgön Tagdrag金刚持在Domä Jema的住处拜新年以图吉祥。
3日,新年仪式完毕,我陪伴宗座去朝拜Domo Kagyu寺,在那里住了两天。接着,宗座和他的随员把休息的地方搬到上DOMO的东嘎(白螺)寺。我们还去Böntsang扎仓的Ngawang Tsöndru寓所、位于东嘎扎仓的僧寮入住。
宗座除了让我担任Tsänzhab Darhän外,还觉得我坐在政府在家部长位列的末尾不合适,于是把我提到排前,让人向我献了哈达,并以那样的身份对我进行了象征性的首次召见。
Katsab Lama Tashi Lingpa Wangchug要求为他弟弟Chagtzö–Manager Gyältän Namgyäl种福德根,于是我为Tashi Chöling闭关处云堂(它是上Domo地区的白螺寺的一部分)内外大约300名听者做了大约15天的《速疾道菩提道次第广论》(Swift Path Lamrim)著述,还在最后做了菩提心法会。
上DOMO地区Galingang Bonpo家庭已经辞世的祖父Tupa Dönyö在世时,我就与他的后代有很深的佛缘,收他们做弟子和檀越,因此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他们家呆了几天,施聚福法,做了长生灌顶和其他教诫。托摩格西仁波切昂旺格桑有非常深厚的佛缘(他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大士,还与白螺寺僧伽有师生关系)。因此我散布了供奉,还供奉了4面带猫头形状贴花装饰的幡,以装点云堂中4根高高的支柱。
3月8日,按照传统举行了简单的8日朵玛仪式,我让我的侍从Palden见见新上任的顶峰道(tsekor)官。宗座嘉瓦仁波切做了勇猛怖畏金刚本心咒(Solitary Hero Yamantaka root mantra)入门闭关、Pälmo派大慈悲者(Pälmo system Great Compassionate One)入门闭关和法王仪式(inner Dharmaraja)。我前往协助进行这些仪式。
派往中国的西藏代表们,包括Kalön Ngapö Ngawang Jigme、Kemä Tzasag Sönam Wangdö、 Kändrung Thubten Tändar及Känchung Thubten Legmön,被迫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随后Ngapö和其中一些代表经由前藏返回西藏,而Tzasag Kemä和Kändrung Thubten Tendar则经由香港和印度、穿过DOMO地区返回。 他们见到宗座时,凭借伶牙俐齿和甜言蜜语,大谈通过“和平解放”和“给大众带来幸福”,并且坚持要宗座及其随员立即返回拉萨。权衡利弊,宗座决定回去。于是,5月初,我们离开DOMO,经过Pagri、 Gyältse、 Nakartse、 Yardrog、 Samding、 Taglung寺、Päldi、 Nyasog、 Zä Chökor、Yangtse、 Nyetang Ratö及Tagdrag闭关处等地返回。西藏政府的护卫队沿途在野地里扎牦牛毛帐篷。我们到Kyitsäl Luding时,政府的主力卫队举行了繁复的仪式,护送我们到了罗布林卡Kälzang宫,沿途行进的循序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情况调整。到Gyältse的本地扎仓宁玛寺,应僧伽的要求,我进行了教诫,只是做了略说,与每名僧人结了佛缘。
前任摄政Kyabgön Tagdrag金刚持已经在我们前头离开DOMO,我去Tagdrag闭关处向他致意。
我们刚到拉萨,珠宝商Kälzang和他的女儿、女尼Anni Ngawang Chötzin——他们住在哲蚌寺果芒院的新屋里——邀我前来,他们还在乃穷山庵(Nechung Mountain)发起了金刚瑜伽母自灌(Vajrayogini Self-Initiation practice)。于是,我去了乃穷山,给那些女尼做了五尊甘达巴(Gandhapa)胜乐金刚大灌顶和四大金刚瑜伽母辛都拉灌顶加持,在那里呆了几天。
Samling一家住在色拉寺在Marlam的Bombor 康村,这家由出家的人做了安排和邀请,于是我便前往,在这一家聚集的时候散了供品,还拿出一点供奉作为资金,资助每年夏季闭关结束时举行庆祝活动。
这后来,应甘丹寺Para Chogtrul仁波切的特别邀请,我去了甘丹寺,并且呆了3天时间(包括用一天时间准备),在Para 康村为甘丹江孜寺和萨济寺扎仓的一大群住持、喇嘛和僧伽做了密集金刚大灌顶。
乡城Samling寺要新建一尊两层楼高的文殊宗喀巴像和几尊贾曹杰及克主杰真人大小的镀金塑像。因为像身要在前藏建造,我就把三尊像的面部(这些是在拉萨特制的)还有心咒供奉送到前藏。后来,当地的寺院按照我的指导建造了像的主体部分和一座文殊宗喀巴庙。
水龙年我52岁。当年3月,宗座嘉瓦仁波切在布达拉宫的大云堂接受Yongzin Lingtrul金刚持做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我也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灌顶。从4月10日开始,应Kundeling拉章的Dawa Dhargye邀请,我在拉萨释德(Shide)庙承担起使命,连续9天给一大群大志愿者进行金刚瑜伽母四大灌顶(Four Initiations of Vajrayogini)、Ngag-tu心咒随许灌顶(且根据诸位密续大上师的传承秘密心咒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在此期间,我还应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的邀请,在准备了一天之后,给他做了62尊鲁依巴胜乐金刚(Sixty-two Deity Luipa Heruka Chakrasamvara)大灌顶。
应上Män(upper Män)地方Chambayer家Tsering Drolkar的力邀,我从5月10日开始,在释德庙云堂,连续约20天,给差不多1000名听众、主要是喇嘛、杜固和格西组成的僧伽,做甘达巴派外五尊胜乐金刚大灌顶、胜乐金刚身曼达拉大灌顶,教诫如何修习甘达巴身曼达拉二次第,以及解说那洛巴六瑜伽(Six Yogas Of Naropa)体验著述。
在罗布林卡宫完成夏季闭关后,我去Tölung温泉疗养。Yarlam Chumig县金碧辉煌的Mägyu扎仓按照夏末的传统,僧众们在法课开始的时候在那里呆3天,于是我散发了供品。密宗行者们开始唱诵修习,我应他们的邀请,简短造访了每一座康村。我还在法座室看见一个小棚子,里面曾住过Kunkyen Jamyang Zhäba和Longdöl喇嘛仁波切等僧人。
接着,我呆了2周进行温泉疗养。两天后,西藏政府的医学星象导师Känchen Kyenrab Norbu还有不丹派Dechen Chökor寺的Gongkar杜固Chögön仁波切及其随员也来了。我与他们二位都很熟悉,有纯净的三昧耶缘。Chögön仁波切对佛法和政治都极其精通,而且能言善辩,而那位医学院住持则对于10个领域的知识都十分专擅,还会谈论经文和讲述前朝旧事等,因此我们在温泉疗养期间轻松的谈话都十分愉快,我们都不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温泉疗养之后,应Tölung Dingka仁波切的邀请,我去了Dingka寺。那是宗喀巴大师的嫡传弟子Dromtsön Sherjung Lodrö的道场所在。我为那里的僧伽做了13尊怖畏金刚和贡利(Kunrig)等大灌顶,而后便返回西藏。
这期间,在与宗座谈论这个话题时,他说我当时应当找人绘制几幅完全达到要求的新唐卡,上面带独勇怖畏金刚、五王和嘉钦雄登五部的图像,以帮助他禅定。因为首席画师Päljor Gyälpo已经收获了怖畏金刚大灌顶,我觉得那已经够了,但还给他做了五王长生灌顶(Life Initiation of the Five Kings)。接着,我把画师升为明王,加持了那些材料和工具等。按照每部密续和经文(如Beu Bum《小集论》等 )的说明,让人备好了几块画布,排好了咒语字母,在五王和雄登唐卡背面写上了长生轮心咒(life wheel mantras)、长生心咒(life mantras)和志愿祈愿文(aspirational prayers)等,在八大神力(eight spirit forces)运行时对唐卡进行了加持,并完成了一切,从头到尾都没有差错。
水蛇年我53岁,应Metra Chötzä Gyatrug的邀请,我在须弥云堂,给1000朵玛僧伽做了五尊甘达巴胜乐金刚和十三尊怖畏金刚大灌顶,其中包括做了几天的预备仪式。
夏季闭关期间,为了动工扩建布达拉宫下部Kagyur印刷室北侧(位于一座新建的庙内),宗座嘉瓦仁波切希望建3座3层楼高的塑像,一个是怖畏金刚,一个是时轮金刚,一个是作明佛母。我吩咐工匠们从头到尾如何完成,从为塑像加持各种材料、升为本尊、检查形状和尺寸,以及在塑像里面供奉心咒等,事无巨细。所有事情完成后举行了3天广大灌顶仪式,宗座嘉瓦仁波切过来撒花加持。
在乡城 Sampel Ling寺举行Gutor投石坐床仪式时,我制作了许多塑像并且拿去展示,主要是法王Yab-Yum、杰宗喀巴、畏怖金刚、Trinle Gyälpo和雄登的塑像,大约有3层半楼层那么高,从上面垂下精美而质量上乘的服饰。
秋天到来的时候,应哲蚌寺果芒院Gungru格西Yeshe Gyatso的要求,我在辉煌的Tashi 果芒扎仓云堂里,给色拉寺, 哲蚌寺和甘丹寺三大寺大约4000名(主要是)僧伽们,如住持、官员、喇嘛和杜固,根据Delam、Nyurlam及文殊语录3部经文(The Words Of Manjusri)合成的内容,做了23天《菩提道次第广论著述》解说。我只是鹦鹉学舌般地讲授着《嘛呢经》,努力在那片智慧大师的海洋当中做着粗浅的解说。这是唯一皈依主帕绷喀金刚持的转世Chogtrul仁波切头一次听讲《菩提道次第广论》。 我还应Ön Gyälsä Chogtrul仁波切的邀请,给僧伽们做了Mati派白文殊随许灌顶(Mati System White Manjusri Jenang)。
10月初,Kashag代表、秘书Kalön Zurkangpa Wangchen Geleg和Kändrung Chöpel Thubten,来到罗布林卡我所居住的地方。他们称赞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和我本人在侍奉宗座嘉瓦仁波切学习方面做得如何出色,并说为表示感激,他们要提升Yongzin Ling到高级老师的位置,而我则承担起初级老师的责任。Kashag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已经共同向宗座嘉瓦仁波切做出这样的提议,宗座已经同意,此事因而确定无疑了。他们用一种专门的方式供奉了曼达拉和3个底座,进献了哈达,表示我必须给宗座嘉瓦仁波切进行所有博大精深的灌顶、口传和教诫佛经与密续,就像向宝瓶里灌水一样。他们非常坚决地提出这样的要求,这真像《现观庄严论》(Abhisamayalankara–Ornament Of Realizations)里所说的那样:
让心灵不要有气馁等等的感觉,
让无我等等得到昭示,
弃绝有害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的,
无论何时、何种情形,都是Yongzin老师。
虽然我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没有这种导师的一丝一毫功德,但我这条老狗还是毫不惭愧地厚着脸皮加入了狮子的行列——我接受了这个职位。
不久,到了象征性地进献哈达、表示下达指令和首次觐见典礼的日子。早上,我在拉萨Trulpay Tsuglakang(化身寺)、密封的小昭寺(sealed Ramoche temple)和布达拉宫圣庙的佛陀释迦牟尼像和其他圣物前做了千供,然后去了罗布林卡宫上层的Jangchub Gakyil寝殿,匍匐在宗座嘉瓦仁波切面前,然后进献了曼达拉、3个底座和哈达。宗座把3个底座和哈达还有一尊文殊菩萨的铜像赐给我。我示意他走进我,然后做了初步的简短解说,开始讲的是生菩提心的功德,并口传了《事师五十颂》本经。
接着,政府在寝殿旁边灯火辉煌的日光会客厅,安排了吉祥的首道宴席。我在席上向一切轮回涅盘之主宗座嘉瓦仁波切鞠躬。他在无畏的狮子法座上光辉灿烂,如同亿万个太阳的万丈光芒,辉煌耀眼,照亮无数众生。我这才真正在首次觐见的时候进献了那3个底座。政府也给了我很高的奖赏。然后,按照习惯,我接受了众位Kalön(大臣)和宗座的随员们进献的表示庆祝的哈达,从首侍和住持直到俗家和受戒的秘书与官员们也都进献了哈达。
罗布林卡的所有仪式结束后,回到拉萨的僧寮,发现门口拿着礼物的人排成长长的一排,都是与我有佛缘和接触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其中有政府大小官员和工作人员,从三大法寺、扎仓和拉章的管理机构往下都有。
当时是Dragyab Chetsang Hotogtu到达拉萨的头一年。他去布达拉宫觐见宗座嘉瓦仁波切,顺便去我的寓所看我。
冬课期间,宗座嘉瓦仁波切做了大量的时轮金刚意曼达拉闭关(mind mandala of Sri Kalachakra),我前去进行协助,完成了事业修正(lärung)入道闭关和弥补不足的火供。
木马年我54岁。那年举行盛大的新年庆祝仪式,以纪念佛在舍卫城演示奇迹,无上大师护法尊者Kyabgön Chenpo Chog宗座嘉瓦仁波切决定要在拉萨化身寺主持一个受具足戒的比丘发愿。在这之前,Dragyab Chetsang Hotogtu仁波切还邀请我去拉萨大祈祷法会云堂,并且在新年活动结束后,按照习俗举行了繁复的仪式,从布达拉宫直到拉萨化身寺顶层拉章上方的甘丹寺Yangtse寝殿,一直不断。我也去了,住在拉章上方的一间屋里。
1月夜晚满月的那天,宗座嘉瓦仁波切,由Yongzin Sharpa Chöje Lingtrul金刚持仁波切任住持和律师(Känlob Dragma)、现任甘丹寺 Tri 仁波切、色拉杰寺Thubten Kunga任告时、我任示密戒师(Sangte Tönpay Lobpön),面对佛尊释迦牟尼,与前任甘丹赤巴、哲蚌洛色林寺Minyag Tashi Tongdü仁波切、江孜寺Chöje、Tsänzhab等人,举行了补充仪式。
面对聚集的10名比丘,宗座主持了一名比丘的受戒和发愿,内容包括接受所有修习的概要。仪式洁净而圆满,没有任何差错。修炼的大功业足以成就他坐床,成为所有修习律藏者的皇冠明珠。我作为戒僧,问那些揭开秘密的问题。讯问整个西藏的精神与世俗领袖嘉瓦仁波切需要无法想象的勇气:“您信仰佛法吗?您不是强盗吗?您是否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等等,但因为这些都是律藏中要求的做法,我还是鼓起勇气问了那些问题。
当天,西藏政府置办了繁复的庆祝宴席,一直排到化身寺大庭院的边上。因为轮到我解说曼达拉供养,我做了大量的解说,从宗座嘉瓦仁波切身语意行的无上功德,一直讲到西藏早期和后来出现的各种流派的《别解脱戒》,直到律藏(vinaya)是佛法根本,既是佛法也是上师等。有人让我从第二天开始,为西藏政府和拉章的俗家官员理事会、在家和受戒的秘书,以及为扎什伦布寺拉章举行的历届传统庆祝活动做曼达拉解说。
荟供法会结束后,Cham Lozang Päldrön请我为去世的Zhichab Pälwa积攒功德根本,我便在拉萨须弥云堂,给大约400名志愿者(其中有许多喇嘛和杜固,如帕绷喀金刚持、Dragyab Hotogtu仁波切,及托摩格西Chogtrul仁波切等)做了金刚瑜伽母辛都拉曼陀罗四大灌顶赐福(Vajrayogini Sindhura Mandala Four Initiation Blessing),并根据合成解说经文(分别是《Molten Sapphire Staircase 》教诫和Zhwalu Känchen所著《Shortcut To Attainment Of Kechara》教诫)对两大次第做了体验解说。
后来,应他们的住持、导师和官员的邀请,并且当时Dagpo Shädrub Ling的僧伽们正要向宗座嘉瓦仁波切致谢,于是我在那座拉萨寺上层的Ewam云堂,给所有的僧伽,对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做了全面的解说。
4月15日,我给帕绷喀金刚持的Chogtrul仁波切接受沙弥戒,并给他取了个Ngawang Lozang Trinlä Tänzin的法名。
中国政府代表Trangchin U几次派信使Bapa Puntsog Wangyäl送来书信说,由于决定在北京召开大会,名叫“全世界人民大法会”(Whole World’s People’s Assembly),需要我们从西藏中部、后藏和前藏派遣代表参加,并且我必须以所有西藏行者总代表的身份参加。因为我不同意,他们就反复不断地请求宗座嘉瓦仁波切,于是他最后命令我接受邀请。眼看不能推辞这个艰巨的任务,我无法说“不”,于是,宗座嘉瓦仁波切带领随员,包括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Karmapa仁波切、小Mindröling仁波切、Kashag、众秘书等人,于5月10日离开拉萨,动身前往北京。我与他们一同前往,随行的有Lhabu、Päldän、Lozang Sherab、Lozang Yeshe及Namdröl。
到Yarlam Drogriwoche的时候,宗座嘉瓦仁波切访问了大甘丹山胜土。当时我向自己所住寓所的神圣底座做了供奉,供了茶水、热米汤,并在大云堂向僧伽散供,还给基金留下一笔钱,因为宗座作为众生之主应邀坐上文殊宗喀巴的狮子法座。我在解说曼达拉的时候做了实物供奉。
从甘丹寺开始,直到穿过Kongpö Ba关口,随员的大多数都是坐的牛车,其余人骑马。接着,因为直到Bowo Tramo的牛车路都没有修好,所有人都骑马,一直穿过Kongpo Gyamda、 Ngapö、 Dru Pass、Zhokha、Nyangtri、Demo、 Lunang及Powo Tongyug等地。沿途都是崎岖的乡野石头路,密林遍布。有时候由于树枝盖得密密麻麻,遮天蔽日。每天都要走过许多陡峭狭窄的道路和溪流。而且那一年的夏天雨下得特别大,雨水多得闻所未闻。大家上山和下山的时候只好步行。上面往往有巨石落下的危险,或者失足掉下许多层楼高的悬崖,摔到下面的岩石上。走过摇摇晃晃、薄如蝉翼的木桥时,激流飞溅的水花打在身上,这样一些情形,犹如Lhodrag的Marpa所言:
到处都是狭窄的小道与河流,
永远走不出浓密的森林……
沿途遭遇的种种危险,
现在想起来,也会不寒而栗。
我们走了大概一个月。那些让人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极其疲惫的崎岖小路,就连上面这些让马尔巴(Marpa)闻名遐迩的诗句描绘的,也相形见绌。
后来,我们在一个叫Powo Tramo的地方,遇到中国的火车,于是上了车。 一连几天,中国人提供的住宿,都是最差的牦牛毛毡帐篷,吃的是修路工人吃的食物。我一边修习这样的密咒——像诗句里说的那样:“对婆罗门、猪狗和难以触碰的东西一视同仁,安之若素!”我与那些工人们用一个容器吃饭,品尝一样的味道。那些马匹、骡子和地位较低的仆人们折回原路,回去的时候路比在Marlam的时候还要难走。
到达昌都 Jampa Ling寺后,我在寂天菩萨(Shantideva)拉章呆了1天;那里已经准备好了住处,曾在拉萨拜我为师的Zhizang仁波切对我进行了非常热情的接待。接着,我们穿过了宽阔的Kamtog Drukha河,又穿过Dege Tro关口。那个关口好像要直通天上。然后我们先后经过Yihlung、Trehor Dhargye寺、Kartze寺、Tau寺等地,到达Dartsedo。
我在Dhargye寺遇见心灵导师Jampa Kedrup 仁波切尊者。他开了一所辩经学校,通过《菩提道次第广论》调服了僧伽们,使他们言行举止勤勉恭谨。我在Beri Lingtog见到了Getag杜固的转世、前世檀越如Zhitse Gyapön家庭,还有我的许多学僧。他们给了我许多路上吃用的东西,可实在是太多了,我只拿了两袋糌粑。
虽然Kartze寺曾作过邀请,并且做好了我去住的准备,可我还是听说自己必须住在中国政府安排的地方。因为Gyapön Trangchin U不容分说地坚持让我们住在中国政府办公楼里,我无法拒绝,只好照办。Zhitse Gyapön家庭的Döndrub Namgyäl父子还有Gyapön Chötze Ngawang Dorje经师来到我住处,畅叙旧情。
当地乡城寺的几名执事包括Lakag杜固都专门来Kartze看我,但中国卫兵拦住了他们,让他们一个月都没法进来。我要走的时候,去了他们住的地方,与他们见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面。
我的侍从Tsongpön Lozang格西和Namdröl从Dartsedo经由Lithang临时回到乡城。我则带着侍从Lhabu、Päldän和Lozang Sherab去了中国。我们穿过雄伟的Arlasen关口,到达一个叫Ya-ngän的中国地区。我们从Powo Tramo直到那里,一路都是整天坐车;我感到头疼、恶心,什么东西不能吃喝多少。因为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Muli Kyabgön杜固、Muli王的大臣还有侍从们都在那里,他们过来看我。
接着,我们来到Drintu,从那里宗旨嘉瓦仁波切还有一小队随员、Yongzin Ling金刚持仁波切、我本人还有Lhabu坐飞机去Shii-ngän。到Shii-ngän的时候,全知班智达仁波切已经从后藏通过北线到了,于是心灵父子团聚了。我与宗座一起参观了拉萨过去佛寺的珍贵佛陀像,只见Jowo仁波切与佛陀的法座空空如也。
然后,我们坐火车到了北京。宗座嘉瓦仁波切Yongzin Ling仁波切和我呆在Yikajao,那里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住处。会见的时间到了,因此我们没有休息时间。开了两天的预备会议。接着,主会开始了。会议开了大约1个月。我们早晚都必须到会。我既不懂汉语,也不懂政治,如此等等,使得这一切变得十分劳神费力。嘉瓦仁波切和班智达应邀参观风景的时候我必须陪同。简而言之,从早上6点左右直达晚上10到11点,除了吃饭时间,我们都是在奔波,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你的善款将悉数作为我们在世界各地弘扬多杰雄登的经费。